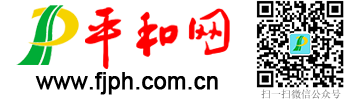自囚与自由
头一年我住的学生宿舍位于宿舍区并列三幢的最后一幢,与食堂、教师宿舍楼、图书馆之间并排成为一条直线。宿舍与食堂之间距离约三十米,再过去的图书馆相距也就百来米。食堂有一个可同时容纳上千人就餐的巨大的长方形餐厅,餐厅的另一端就是通往教学楼的水泥通道,且与第一幢学生宿舍楼平行。宽敞的餐厅后来被隔出一段作为舞厅。第一幢学生宿舍楼住的是学长们,他们在楼前与餐厅之间的通道上接待了新生,而后,在这个公共地段经常摆上一张桌子,一台黑白电视机为大家播放女排争夺五连冠之战。可那时候我融不进这个沸腾的大锅,因为学长们安排的电视和座位,我只能在外围踮起脚尖看,可怜耳边虽然灌满了掌声和喝彩声,饥渴的眼中却只有一些跃动的人影,我附和人群的热血和冲动随着脚酸脖子累而迅速冷却下来:这些热闹不属于从山里出来的我!就更不用说那个每逢周末就灯光迷离的舞厅了。
于我而言,食堂与图书馆都是我进食的地方,食堂打理我的肚子,而图书馆喂养我的脑子。于是,课余时间里我按照学长的指引,来到了图书馆。这里是个偏僻的角落,门前矗立着高大的霸王椰树和婆娑的凤凰木,还有冬青围成的篱笆。图书馆内静悄悄的,学长们或正襟危坐,看书,在阅读卡片上急速做着读书笔记,或起身到借书窗口领取另一本书,偶尔有一声椅子搬动的声音都像是响雷。但我却感觉到这里静悄悄的氛围中有一股激流在潜藏涌动,于无声处有一阵阵激烈的喝彩在酝酿,这里仿佛有一千颗一万颗古今中外的心在默默交谈,有一千双一万双眼睛在书里书外含情脉脉地对视。第一次进入图书馆,我空手进去,空手出来,因为我还没领到借书证,我仿佛是个新入行的贼在踩点,被主人的奢华与典雅所震慑,我相信在这里随便出手都可以取到令人垂涎的东西,这里必定是我长期落脚的地方。
没过几天,我的那段简短得只有三年的阅读生活开始,就在那个小窗口,我的借书卡递进去,五本书从里边递出来,那情形颇像电影里的囚犯端着铁盆子走过分饭的窗口。有位学长给我开过长长的书单,我读了其中一部分,我根据自己的口味予以取舍。忘了是什么时候开始,我尝试着把自己的一些想法付诸文字,竟也陆续被贴上学校征文的阅报栏,又因此获得了一本特别评论员证件。比之借书证必须在小窗口取有限的五本,凭此证可以登堂入室直抵心脏,到森林一般的藏书架前任意挑选、浏览旧书或新书。我的责任就是选择性阅读并作出相应的评论贴在阅报栏,把湮没在海洋中它或它们推介给更多的读者,为读者提供阅读方向。随同我去漳州念书的一只绿色军用挎包此时发挥了作用,我珍视机会,一整套一整套地搬书。
我在图书馆读书的总时间其实不长。图书馆太静了,稍微一点动静都会把我从书城中惊醒,而且图书馆终归是公众场合,不可能给你一整块绝对安静的时间和空间,于是我才把书带回宿舍,强迫自己学会闹中取静的阅读方式,舍友的谈天喝茶是与我无关的。我的下铺是个带着1500度近视镜的家伙,夜里十点熄灯后,他还点着蜡烛继续读书,这一点一开始我很反对,我觉得作息时间要动静分明有规律才好,只是后来自己碰上了喜爱得不得了的书时,也是夜战到凌晨两点,直到强迫自己合眼睡觉,还心驰神往于书中的异域空间,这才体会了他的心情。宿舍里其他几位同学各有自己的阅读倾向,偶尔会展开论战,我是从来没有参与的。我总觉得自己力量不足,武器装备不够,不配与人博弈。我更像一只慌里慌张的猴子,一直逡巡在诗歌大树、散文丛林、小说海洋之间,急匆匆地采撷营养,不管是伤痕文学还是寻根文学,不管是乡土的还是学院的,也不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
我甚至把文学类书籍带到课堂上,把自己埋在喜欢的书页中。我非常感谢20世纪80年代中期高校的课堂制度,老师只管灌输而少有提问,使我避免了许多未知的尴尬。我因此每次期末考试时都很紧张,用大约一周的时间翻阅遍整个学期的必修课,所幸都能通过。唯一需要补考的科目是古典文学常识,当时的助教蔡阿聪老师有一次聊天时告诉我,“你本来这学期开学前要来参加补考的,是林博士说你的古典诗词欣赏评论文章写得精彩,特意给你赦免了。”他若不说,我竟不知此事。
过度自囚于感性而柔软的文学空间,以致疏忽了对硬性常识的必要把握!然而吉人自有天相吧,我竟又因自囚而获自由! 从此我相信,成天陪伴书本过日的人到达幸福彼岸的方式跟平常不读书的人是不一样的。世人皆苦于“心为形役”,只有读书人因自囚书城而最终获得了心灵放飞的多维空间。自囚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没人知道,我只谨记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在他的著作《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一部开篇之处,借约翰·米希尔面对新生孙儿克利斯朵夫说的一句话:“好媳妇,得了罢,别难过了,他还会变呢。反正丑也没关系。我们只希望他一件事,就是做个好人。”
面对浩瀚书海,我们每一个人每天乃至永远都是丑陋的新生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