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粉的乡韵
米粉的乡韵
⊙黄 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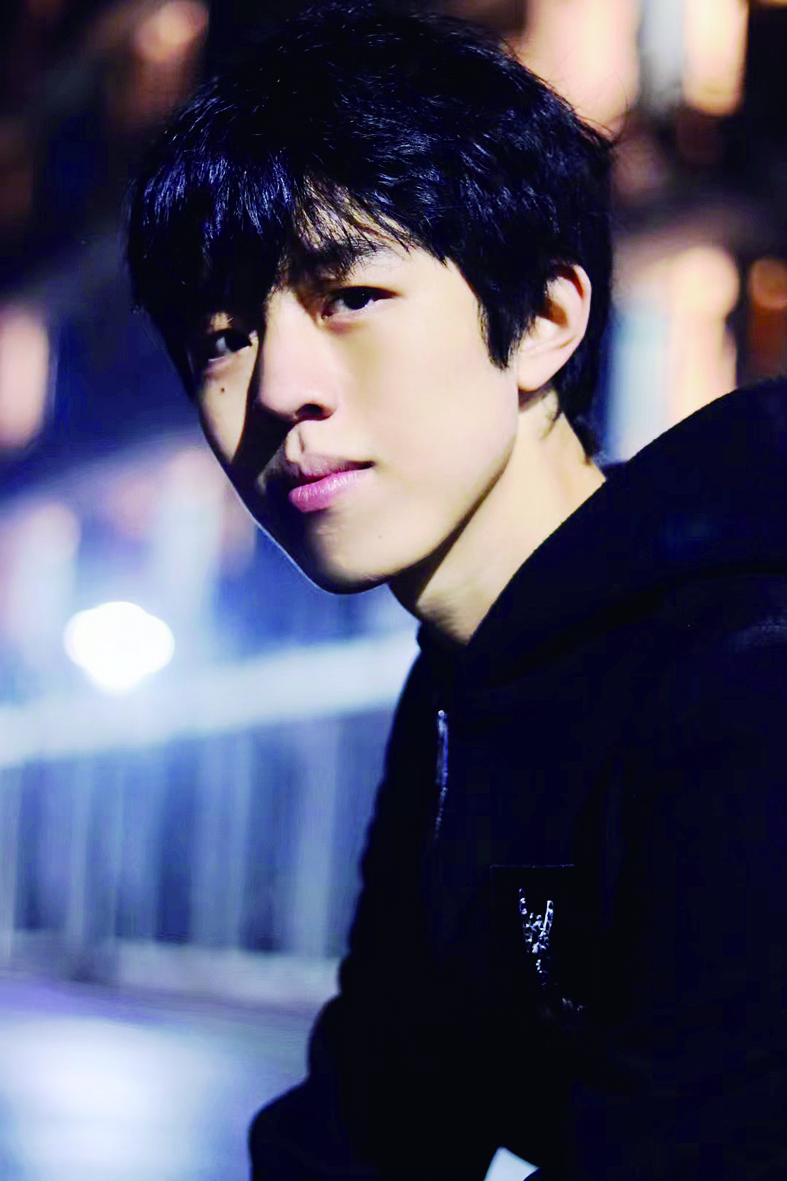
作者简介:黄飙,男,平和人,在读大学生,福建省作协会员,作品散见于《福建文学》《生活•创作》《闽南风》《闽南日报》等刊。
每次看到广西舍友将一大碗螺蛳粉像坐滑梯似的吸溜进他的腹中时,我都会想起家乡的米粉。
家乡的米粉和螺蛳粉大同小异,但它更细更长,且更 Q。相比之下,螺蛳粉显得像个粉嫩的大棚蔬菜,而平和老家的米粉则更像是自然生长的野菜。且不论其优劣,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几乎所有人都偏爱家乡的美食,那从娘胎带来的记忆具有不可篡改的先天优势。上大学前,家里隔三差五就会吃米粉,如今日子好了,想吃啥就吃啥,不像父亲说的,以前只有过年过节或者客人来时才有米粉吃。父亲小时候,他的几个舅舅每到年底都会到家里来,回去时总是一头挑着鸡鸭,一头挑着米粉,父亲说,米粉是他童年时必备的年货。
米粉是稻谷的产物,在我老家,过年还愿、祭祀、拜祖宗时都会有一盘米粉,乳白细长的米粉是代表丰收的谷物,用它祈祷年丰物阜的美好愿景正合适。当然,团圆饭更少不了一盘炒米粉,不管有多少山珍海味,代表谷物的米粉永远是年夜饭的主角,把它往中间一摆,便有一份团聚和未来长长久久的寓意。在老家,米粉延伸了人们对食物的精神追求。
现在想起来,最令我怀念的还是高考前的夜宵。每晚十点半,估摸我快离校回家了,父亲便骑着小电驴上街拎夜宵,俗称状元宵。其实几乎所有的家长都如此,谁都不愿孩子输在一顿宵夜上。为当好考生家长,身为记者的父亲放下案头工作,每晚都会用保温桶为我准时拎回夜宵:馄饨、水饺、拉面、拌面、炒面、面猴等。虽然每晚都换口味,但很快我就吃腻了。不知道是压力太大还是胃口不好,本来挺爱吃面的我,那阵子一改常态,一看到面食就有一股油腻堵在喉结。看我每晚皱着眉头吃宵夜,父亲也蹙起了眉结。我知道那阵子他跑遍了县城的大街小巷,极少吃宵夜的父亲,几乎把县城的小吃店摸个透。由于疫情,我们这届高考推迟了一个月。别小看这一个月,夏日的闽南,多熬一天都是艰难的。
立夏一过,不要说夜宵,连正餐我都没胃口,每餐都是扒拉几口做做样子,这一切自然逃不过父母的眼睛。那晚,我昏沉沉地回到家中,想冲个凉就睡。父亲却对我说:“今晚的夜宵不一样,你尝尝。”刚拧开盖,一股热气便冲出来,随着热气,那股酸爽的味道直扑向鼻尖。父亲为我拿来一个大碗盛米粉,说今晚是咸菜煮米粉。咸菜是我们这里的芦溪咸菜,米粉是地道的大溪米粉,这两样都是我们当地拿得出手的土特产。咸菜的酸爽加上滑溜的米粉,这顿夜宵让我胃口大开,吃得大汗淋漓,有股通透的感觉。看米粉对我口味,从此,父亲常拎米粉夜宵回来,有时是煮米粉,有时是炒米粉,渐渐地,胃口又好了起来,米粉成了高考记忆之一。现在回想起来,米粉无形中给我带来福运,它打开的不仅是胃口,让我有更充沛的体能迎接挑战,还有流淌的父爱,它沉淀在我心底的是满满的幸福!
今年正月,想到转眼又将开学,猛然间又想再尝一下高考前夕的夜宵米粉。我骑着车,穿过窄窄的中东街,又绕过七弯八拐的民主街,终于在九一七街和建设街的交汇处找到一家米粉店。一打听,正是一家用芦溪咸菜煮大溪米粉的小吃店。不管它是不是父亲给我拎夜宵的米粉店,我决意品尝一下。
我看店主拧开小炉,用一口小锅舀小半盆汤,再加上咸菜、鸭血、牡蛎、瘦肉和一碗米粉拌煮一会,出锅再撒上一把芫荽,一碗热腾腾的煮米粉便端到我跟前。我吹口气,舀勺汤一尝,正是心底的那股酸爽味道,再挑一筷细长的米粉入口,滑溜、细密、弹牙,蛰伏的味蕾次第绽放。顾不上斯文,在寒雨迷蒙的春夜,一碗热腾腾的煮米粉下肚,感觉真痛快。
但我深知,开学后,我对米粉又是新一轮的念想。米粉已走过千百年的历史,起码在八山一水一分田的闽地,祖祖辈辈的人因能吃上一碗米粉而倍感幸福。米粉,在我的家乡是一缕难以抹去的乡愁,从小就习惯吃米粉的我,长大离乡后才深切地明白,每道美食都有它的韵脚,都有自己独特的乡韵。家乡米粉的乡韵,是团聚、长寿、欢庆的载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