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世家满门英杰 阅百年抗寇风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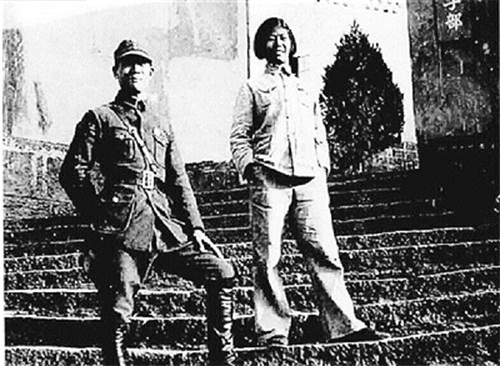

雾峰林家——台湾五大家族之一,其跌宕起伏的家族史在台湾家喻户晓,台湾史学者黄富三教授曾著文:“雾峰林家是台湾二百年来的第一家族,其家族的历史就是台湾近代史的缩影。”意谓林家家族史与祖国大陆、台湾宝岛的近代史同步发展,是以浓墨重彩绘就,百年世家如何在国恨家仇中扎根求存,力谋发展的传奇长卷。雾峰林家在抗英、抗法、抗日中艰难前行的家族史,无不浸润着海峡赤子反抗入侵的满腔热血,及林家英杰忠心爱国的忧患情怀。
汉土之邦何时复
清朝乾隆十九年,漳州府平和县埔坪村的林石(雾峰林家第一代)不畏艰险,东渡台海,肇基“雾峰林家”。后雾峰林家第二代林逊早卒,第三代林甲寅,衍林定邦、林奠国、林振祥三子。清朝道光年间,林定邦开枝雾峰林家下厝系,子孙多务农习武,以鼎盛武风奠该系之根基。鸦片战争期间,林定邦(雾峰林家第四代)及长子林文察(雾峰林家第五代)曾协助台湾兵备道姚莹,率乡勇击退侵台英军,虏获敌军300名,双双被誉为“抗英英雄”。此后林文察积极捐银助饷,募乡勇随征小刀会,首立战功,进而平匪乱,征闽浙,平定戴潮春事件,屡建功勋,由游击擢升至福建陆路提督,可谓军功赫赫,曾国藩曾赞言:“闽中健将,文察为最。”后值太平军攻陷漳州,林文察赴调平乱,终因血战捐躯漳州万松关。清廷为慰忠灵下旨拨银,在漳州府城和台湾雾峰两地,各兴建“宫保第”专祠供后人凭吊,可谓极尽哀荣。
林文察殉职后,其子林朝栋(雾峰林家第六代)世袭乃父云骑尉之衔。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刘铭传抵台主持海防,法军进逼台北时,征召兵部郎中林朝栋。林朝栋亲率500乡勇北上抗敌,多次击退法军。首次月眉山激战,助战有功;第二次月眉山之役为唯一未被击溃的部队,掩护主力成功回防。基隆狮球岭一役,林朝栋夫妇更是联手击退法军,大振军心。刘铭传对林朝栋及所部的戮力征战,大为赏识,战后全台30多营乡勇被裁撤,独林朝栋与张李成两营被纳入清廷正规军队。林朝栋营即为日据时期,台湾抗日武装重要力量之栋军肇始。
此后,林朝栋调度有方,辖下栋军积极参与修路筑城、抚番屯垦,兵力也逐步扩充至十营,成全台最具战斗力的部队。施九缎乱事之平定,更令刘铭传对林朝栋大为推许,奏请清廷“赏穿黄马褂,以示优异”,时林朝栋以道员身份着黄马褂,全国罕见,恩荣备至。
甲午战争爆发后,1895年清廷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条约中将台湾全岛及其附属岛屿以及澎湖列岛悉数割让日本。此丧权辱国条约一出,林朝栋义愤填膺,不愿臣服,他将家眷送至厦门,只身留台,筹划迎战事宜,欲与日军决一死战,甚至于府邸前摆满油桶,若战败就火烧全宅。时台北在台湾所属三府中,战略地位为最,驻军不下五十营,且“兵力雄厚,铜械充盈”,由被推举为台湾民主国总统的台湾巡抚唐景嵩亲守。狮球岭则为攻掠台北必由之路,省会之屏,原由林朝栋率六营栋军扼守炮台,栋军曾据此抗法“地势险要甚悉”,“且训练有法,颇负时望”。怎奈唐景嵩偏倚亲军广西乡勇,加之部署失当,将栋军调防台中,及至战机紧迫,才急令林朝栋回援,惜为时晚矣。守军溃败、基隆沦陷、台北失守、唐景嵩卷款潜逃等等,无不牵制全台抗日斗争,使形势急转直下。终令林朝栋徒留满腔遗恨,奉旨内渡,后再组栋军,无奈未能再踏足台湾。临终前其仍嘱子弟,圆未竟之志:“我惟一的愿望,就是有一天你们能够从日本人手里收复这汉土之邦。”而其麾下的原八营栋军,则秉其抗日遗志,投身台北、台中战场,成为台湾抵抗日军的主力之一。
大汉之民何能辱
林祖密(雾峰林家第七代)承袭其父林朝栋之志,嫉恶如仇,胸怀民族大义。林家迁居厦门后,林祖密受乃父委派,返台处理家业,时值日本以武力占领台湾,严令凡未在规定时限内离台之台胞,自动变更为日本国籍。为不受异族统治,林祖密多方周旋,才得以借回厦门奔父丧之机,向日本驻厦门领事团申请放弃日本国籍,恢复中国国籍,获发中华民国内政部复籍执照,号码为“许字第一号”,成为日据时代首位复籍的台湾人。因为林祖密世家子弟的身份,日本人对其脱籍许以高官厚禄相留,但其执意如此。据台日本当局因此强行没收林家2万多甲山林,2000多甲水田及五六百家的樟脑厂、制糖作坊、糖铺。林祖密共计九成家产冰消瓦解,但爱国甚于爱家的林祖密不以为意言:“大汉之民,何能因财富而受辱于倭奴。”在此期间,林祖密以抗日复台为念,积极推进拒买日货,及收回鼓浪屿租界万国公地等反日运动;更秘密资助了多起台湾抗日武装起义,如罗福星起义(苗栗事件)、余清芳领导的噍吧年起义、张火炉起义(大甲、大湖事件)等,虽星星之火未及燎原之势,但其抗日爱国之诚可见一斑。
林祖密内归后,在福建积极投身反袁护法运动,捐饷50万银元,自组闽南革命军,被孙中山亲命为闽南军司令,授少将衔。还响应“实业救国”号召,从事垦牧、开矿、水利事业,为漳州基础设施建设出资出力。1925年8月,林祖密遭反动军阀于华安设计杀害,不幸英年早逝。
国土未复心不歇
由于深受家庭抗日氛围熏陶,林祖密第五子林正亨在“七七事变”后,毅然投笔从戎,考入南京陆军军官学校,专攻防空化学,毕业后被分配至第5军军部当见习官。1940年,林正亨随部赴广西作战,任96师参谋处少尉军官,在军队开赴前线前,其在戎装照上,题词《满江红》一首“戎装难掩书生面,铁石岂如壮士心,从此北骋南驰,戴日月,衣霜雪,笑斫倭奴头当球,饥餐倭奴肉与血。国土未复时,困杀身,心不歇。”以明誓死抗日心志。在大型抗日战役——昆仑关大战中,林正亨带领情报排,与敌军激战四天四夜,身负重伤,所幸冲出包围圈。战后因表现英勇,被晋升为中尉连长。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国为打击日军形成统一部署,国民政府方面组建远征军,赴缅协同盟军作战。林正亨所在部队随之转战缅甸,其辞别临产的妻子,义无反顾地踏上异国的征途。历经缅北、缅中的多次作战,林正亨升任远征军新1军步兵团上尉连长。在攻克缅甸西北重镇——八莫战役中,林正亨率所部追击败退日军,却遭日军绝地反扑,展开肉搏血战。其一人奋勇杀敌数名,终因身负16处刀伤重创而倒地昏迷。幸得援军增援,消灭日军残部,并在清理战场时,从血流成河的尸堆中,发现尚存一息的林正亨,并将其送往缅甸后方医院。经美军军医的两次手术施救及4个多月的住院治疗,林正亨挽回生命,然而脸部、手部、背部多处伤及,双手手筋受创最重,形近全残,惟右手尚能勉力握笔。1945年林正亨出院后,用蜷缩的残手,写下征战八年来首封告慰其母的家书,“在这神圣的战争中,我可算尽了责任。台湾的光复,父亲生平的遗志可算达到了,要是有知,一定大笑于九泉。我的残废不算什么,国家能获得胜利强盛,故乡同胞能获得光明和自由,我个人粉身碎骨也是值得。”信中字字血泪,将民族大义高置于个人安危之上,着实可钦可佩。
后来,经由妹妹林冈指引,林正亨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1946年,带领20多名台籍青年重回台湾,开展工人运动,并积极参与了台湾民众为反抗统治当局爆发的 “二二八”起义。起义失败后其辗转广州、香港,加入台盟。次年,林正亨再次回台,建立秘密交通站,印发《综合文摘》《和平文献》等进步刊物,宣传台盟主张。正当其为革命奔波之际,却遭叛徒出卖,被冠以加入中共外围组织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的罪名,遭到逮捕。蒋介石念其为林祖密之子,曾派陈诚到狱中劝降,但林正亨矢志不渝。临刑前其在狱中地板直书《明志》诗:“乘桴泛海临台湾,不为黄金不为名。只觉台胞遭苦难,敢将赤手挽狂澜。”就刑时,林正亨年仅35岁。1983年,国家民政部特向其家属颁发“革命烈士证明书”,以表彰林正亨终其一生为洗血国耻、保家卫国而倾尽己力的事迹。
述及雾峰林家,自清朝乾隆年间肇基先祖林石,冒险渡海,扎根台湾,至林家第三代林定邦兴建下厝宅邸,被尊为该系始祖,该支子孙即以武略昭彰、武杰济济奠下厝之根基,逐步造就雾峰林家家大业大的世家传奇。林家族中子弟实则蒙受祖业荫蔽,尽可衣食无忧,但其血脉中奔腾的是爱国甚于爱家、受侵奋起抗争之血性,令数代林家人从未选择安于富贵的人生坦途,他们不论投身台湾早期的抗英、抗法、平番、复土反日运动乃至祖国的抗日战争,每一次的保家卫国、维护统一,雾峰林家后裔都是倾家资纾国难,披甲上阵,力拼血战,其屡仆屡起的家族发展史可谓百年罕见,为御外侮不计个人得失的满门英杰,更是彪炳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