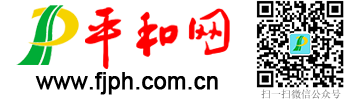江南
编辑按:
壹
第一次拈一枚雪白轻盈的蚕茧在掌心,初夏窗前,车水声中,梦回以后。捧住这新生的珍贵缠绵,不由得想起华夏土地上千百年来的浣纱、纺绣……甚至可以想象自己已经捧住了一整件羽衣霓裳。不过,笙歌还来不及,旋即就又痛到义山的相思与寸灰。
暮春田间,四处问访桑树何在的辛劳还在心头。想到胡兰成笔下有桑叶、竹笋和月光的浙东,忍不住又想到张爱玲去温州找他,远远地倚在舢板栏杆上望着将至的前方说:“因为他在那里,我感觉一整座温州城都像含珠一样闪闪发光。”再想到自幼吟诵着《江南春》与《桂枝香》的迦陵先生,漂泊海外大半生,以燃烛之热忱投入祖国古典诗词,为异族的学生们一再深情解释古老中国的“烟柳画桥”与“风帘翠幕”,自己却年逾古稀,才第一次有机会踏上宋词中熟稔了千千万万遍的江南。
迦陵先生说,词之美在于曲折幽微。曲折幽微,不正如人心吗?正如一枚春蚕之茧,一根细线,千回百转,看似严丝合缝层层内敛,却又并不是不可以在某一个恰当的时刻,以一种恰当的方式,牵出一个由头,抽丝、剥茧。梭如光阴,来来回回,心中的经纬,逐渐铺陈。往事若要挑出一匹来,染色成绢,请许我蘸一笔绿沈,以此浓重饱和春夏之色,寓意江南。
贰
要许多许多桑叶,才能被一只蚕,在暗室中耗尽终身,凝成一根漫长细丝。如同一个人,蒙昧仓皇置身尘世,要咀嚼亦或者狼狈吞咽多少内涵丰富的日子,疼着消化不良的胃,在许多许多个不眠的深夜中去反刍、辗转,才有可能在某一个黎明之前,抓住些许游丝般的答案。
要以一颗温暖的心,安放在一个不再消瘦的身体里,去江南。要在火车上看地图,密密麻麻的路线像迟钝已久的神经网路,每一个地名唤醒一个节点。——所有的远方都是别人过腻了的家门前,我懂得,不要真以为我会误会,这一路过去即将惊见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但,这并不重要。江南,它穿过一场漩涡一般令人涉足就注定淹没其中的文学史,早已不再是一个地理名词,而是这场历史中一个独一无二、美丽哀愁的意象。江南,是几句话他在几百年前留下了,几句话你在几百年后惊心了,这两者之间的一份深深懂得。
在明故宫的城墙下,用掌心一寸一寸摩挲过那些斑驳生苔的陶砖,辨析有些砖头上烧制的作坊商号和掌柜姓氏,怅然凝噎。我这么一伸手就贴近它们了,还可以随便拍上几张照片。可是,我心里明白,我与它们是隔着多少兴亡,人事离合的层层叠叠。看山看水纵然是好啊,可惜终究不如如此,装几段故事,千山万水找到历史的残迹,默默地坐下来,喝一口水,怀想。
中国的修史传统自古严谨,或许是面对悠悠苍天,亘古日月,祖先们自觉个体的生命实在太过短暂,便只好以一代又一代延续无尽的历史感来宽慰心怀。江月年年,长江流水,金陵果然是最宜怀古的。从两千多年以前卧薪尝胆的石头城,到一千七百多年以前浪花淘尽英雄的东吴建业,再到一千年前曾车如流水马如龙,雕栏玉砌又终不再的南唐……所以,病逝于斯地的临川先生,两度罢相之后,大约终于化激奋为沉郁,在某个萧瑟晚秋,于千里澄江似练的长江边,写下了“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的千古绝唱。当他离世,走进多少因他而改变过流向的历史长河之册页,历史本身自然不会停下脚步。1368年,洪武大帝赶走蒙古人,将大明帝国定都南京。但他的儿子永乐皇帝即位以后迁都北京,在北京城修筑了令友邦使者想要朝觐中国君主,不得不走得气喘吁吁方能遂愿的紫禁城。可惜,两百多年以后,李自成逼死了崇祯帝,清人鸠占鹊巢,坐上了太和殿的龙椅,建康城前朝故宫的宏伟壮丽,从此在历代的兵灾战火中分崩离析。彼黍离离,彼稷之苗,残存的宫殿柱础,四周野草蔓芜。
三百年前,曹雪芹在这座遗址之畔的某一座宅院里出生,学步学语。在那部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的著作里,他念念不忘让甑宝玉住在金陵。曹雪芹出生后不久,吴敬梓寓居秦淮,在《儒林外史》的市井生活里铺陈了清中叶江宁城的纷纷场景。又过了两百多年,余光中先生在南京出生,上小学。抗战爆发,他在战火中失去家园,随着母亲一路流亡到四川,再后来是异国他乡。回忆故乡他写到:“杏花。春雨。江南。六个方块字,或许那片土就在那里面”,他也记得养蚕:“在江南的泽国水乡,一大筐绿油油的桑叶被噬于千百头蚕,细细琐琐屑屑……”。
从曹雪芹到余光中,一回首,就是三百年。从李璟、李煜、冯延巳到余光中呢?竟然已经一千年!可是如果我望向书柜,我却可以看见他们相距很近,咫尺之间。文学的魅力在于,它可以从臃赘的人类历史中轻易就脱颖而出,略过时间与空间,略过尘世恩怨情仇,甚至略过作家本身,永恒成一颗一颗亮晶晶的星星,镶在不眠人的夜空里。正如此刻,它们纷纷静默地伫立在不同的城市里,不同大楼的不同房间,不一样的书柜里。兵荒马乱,只能毁灭王朝与宫殿,却消损不了文学。且人世悲欢,恰恰能让每一句穿越千年的诗与词,都带着作者的体温与心跳,眼泪和叹息甚至血泪,完整如初地抵达另外一个读者的心灵。
如果一条河、一座城,不曾被一颗丰盈易感的心灵低吟徘徊,它们纵然赏心悦目呵,终究只是无心的风景。但是寻常的阡陌,屋瓦人家的桃花,却可以因为几句诗,从万花丛中独树一帜,自西周一路热烈盛放到如今。春天来得比蜀中更晚的长江以南,就因为它是一晌贪欢的江南,是日出江花红似火的江南,它就值得被一个懂得的人所向往、流连忘返。
我们爱的,本非万物,仅仅是万物所承载的深情。
叁
如果江南只是一个朦胧意象,钟情于这个意象的人,难免分不清楚江苏与浙江,分不清楚那些近似的地名应该归属于哪个省份。我们只需要晓得,那里水气氤氲,遍地风流,那里有这两百年以来最耀眼的文人墨客,最传奇的才子佳人。
要确认过无数次,才讶然发现,原来王羲之、陆游、鲁迅和胡兰成,他们都是会稽山阴人。四川盆地的气候,每年最冷的时候只有一周,在冬至过后,摄氏六度左右。可是,想不到立春将近的浙东,湿冷阴霾超乎家乡的冬至时节,最冷的那天,我把本来用来换洗的两条打底裤和一条牛仔裤,合三为一穿到了一起。
难忘绍兴站灰蒙蒙的天空和一地的冷雨。我往手里呵气,暗自感叹,这真是酝酿《故乡》与《祝福》的最适宜天气。当年鲁迅先生从水路回家,大约也衣衫单薄,才忍不住回头在《故乡》里写下:“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阴冷寒湿带上一点文学氛围,意味也就与众不同了,我愉快地把不适视为了享受。再忆及张爱玲在《秧歌》和《异乡记》里浓墨重彩的描写寒冷,讲的正是旧年腊月到新年正月的两个月里,浙东乡下难耐的严寒,以至于新下乡的青年作家顾刚,没有火炉竟然冻得无法入睡。如此回味一番,不但安心享受起这份天气,简直还要庆幸自己准确地选择了这样一个恰当的时间来到江南。
拦一辆出租去鲁镇,听司机用浙江口音浓重的普通话热情介绍绍兴美酒与风物,不忘叮咛我们来回乘车事宜。汽车穿过大片并没有作物生长的田野,我望着车窗外赭赤色的泥土,一整颗心都被温暖。从兰亭回城里,与游客拼车,一路上全程收听一位当地阿姨与司机相互打趣,从最初的茫然到后来的明白,不禁莞尔。之前喝过的一点绍兴黄酒刚好上头,我一遍遍在心里默念他们咬字的音节,像用手指一粒粒摩挲过一串温润珠链。藉此,沈园带给我猝不及防的惆怅,才算渐渐平息。
肆
几年前在华清池,越往里走,《长恨歌》的句子在心头敲得越疼。红尘路窄,竟窄到一位曾呼风唤雨、四面来朝的君王,要亲手将心爱的女人推出门外。人在江湖,终究是如此无力、无助、无辜,而尴尬的存在。我的整个西安之行,从那一刻起,深深陷入“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心酸与迷惘。
而沈园来给我的沉痛,犹有过之。
南宋半壁江山,文人武将,莫不切盼收复失地,其中可歌可泣者,数不胜数。倒是放翁,一生执著,最后落得个“爱国诗人”的名声,让人潸然。是啊,稼轩、岳飞、陈亮、文天祥……他们亦曾以诗明志,留下千古名篇,可是他们不以“诗人”名世。他们亲身披甲上了战场,天命人事的博弈之间,他们一腔热血交付了所有,求仁得仁。可是陆游,他没有得到这样的机会,“江山不尽英雄恨,天意无私草木秋!”
陆游一生写过许多有关梦境的诗词,梦中他总是听见金戈铁马,剑鸣鞘中。四十九岁尚在壮年的陆游,任职蜀中念念不忘抗金:“逆胡未灭心未平,孤剑床头铿有声”,翌年他又叹息担忧:“国仇未报壮士老,匣中宝剑夜有声”。然而,漫长的二十六年过去了,壮志未酬,英雄终白头。七十六岁的陆游归老山阴,已倍感怆然:“万里关河孤枕梦,五更风雨四山秋。”
光阴不饶人,严相逼,我甚至有些以为,放翁能长寿至85岁,就是因为他不甘心,望眼欲穿有期待。要把他的诗词从年少意气风发,一路读到他年迈于时局无能为力,才会在面对《示儿》时,心如刀绞,泪流满面。再回想他在47岁时,于蜀中路过剑门山避雨,曾不甘心地自嘲“此身合是诗人未”?想不到最后,他真是个诗人,修饰语还是“爱国”。
陆游一生所倾情者,无非收复国土和怀念旧爱。多年以前我就曾想,如果我要以陆游的复国理想写一篇文章,题目就该叫做《铁马冰河入梦来》。很感念沈园的管理者,重门之后,曲苑尽头,他们在陆游纪念堂前,安放了两座相向的雕塑,一座是陆游像,另外一座,正是一匹铁马。
当然,千古伤心之地沈园,承载的并不是陆游的复国理想。
1144年,二十岁才华横溢的陆游迎娶唐婉,夫妇二人情投意合,如胶似漆。可是陆游的母亲不喜欢功名未成的儿子被儿女私情过于耽搁,渐渐不喜欢唐婉。他们婚后不足三年,陆游就被迫休妻,佳偶无奈分离。1147年,陆游娶了第二任妻子王氏,唐婉也再嫁给当地另一位名士赵士程。如果不能相濡以沫,相忘于江湖也是很好的。可惜在1155年的春天,31岁的陆游与唐婉,却在沈园不期而遇。一别经年的故人,发乎情、止乎礼的分一瓿薄酒,这些年的心事有口难言。唐婉离开之后,作为诗人的陆游,不耐感慨,挥笔在沈园的墙头上写下一阕《钗头凤》,怨世事弄人,叹离情难寄。
春寒的绍兴,沈园里的植物还残余着严冬的凋零。我着急想去看那面刻着《钗头凤》的墙头,已经穿过了两道园门。没料到第二道门内,流水蜿蜒,九曲回肠。我踏上石桥,望脚下流水,一刹那就痛彻了陆游在75岁高龄之际写下的那两句诗:“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
如果陆游与唐婉的故事,以第一首《钗头凤》戛然而止,我想,中国文学史上,不会出现陆游后来以沈园和唐婉为主题的那么多比《钗头凤》更深情悱恻的诗歌。如果爱情的难题,只在于有情人不能长相厮守,以时间之灵,倒还可以消磨一切心头不平。可是,如果在一场不能厮守的爱情里,一个人竟然为另外一个人付出了生命,时间于生者,当然就不可能再是抚慰的灵药,而变成历久弥新的折磨。
悲剧逐渐走向高潮,唐婉于惊鸿照影的翌年再度游历沈园,惊见墙上陆游所题之词,“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邑鲛绡透。”前尘往事,排山倒海向她袭来。哀愁恍惚中,这位情深义重的女子泣血和了另一首《钗头凤》之后,竟然在当年秋天郁郁而终!
唐婉因为自己而早逝,让陆游陷入无尽感动与愧疚之中。他一生的情感世界,从此被这位用整个生命来爱过他的女人,深深萦绕,至死方休。1188年,64岁的陆游从严州任满归山阴,沈园依旧,前尘隔海,他写下第一首怀人之诗:“唤回四十三年梦,灯暗无人说断肠。” 那一年,距离他和唐婉初婚,已过去四十三年。年逾花甲的陆游在宦海中又经几次起复,直到73岁才彻底罢官回乡。回到山阴之后,他在沈园墙下哀叹:“坏壁醉题尘漠漠,断云幽梦事茫茫。”故乡生活使他常近沈园,旧事旧痛无以回避,终于在两年之后,75岁的陆游写下被陈衍在《宋诗精华录》里称为“绝等伤心之诗”的《沈园二首》:“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81岁,白发苍苍的陆游“路近城南已怕行,沈家园里更伤情”,因为他感慨“玉骨久沉泉下土,墨痕犹锁壁间尘。”82岁,残年的陆游踱步到沈园门口,发现园门被锁,担心当年的《钗头凤》已被灰尘和青苔浸蚀:“尘渍苔侵数行墨,尔来谁为拂土墙。”85岁,江南草长莺飞的春日,风中之烛的陆游最后一次来到沈园,就像同时为子孙写下《示儿》一样,他为自己缠绵一生的爱情写下绝笔:“沈家园里花如锦,半是当年识放翁。也信美人终做土,不堪幽梦太匆匆!”
我总是容易被深情执著的心灵所感动,无论他的燃烧是为了理想还是爱情,陆游竟是兼而有之,春蚕至死,蜡炬成灰。我并非不钦佩智慧的云淡风轻,可是我觉得,真的淡泊,背后一定是情深的汪洋大海。渡得过来,才看得明白。
伍
灯下。窗前。
南京的梧桐,兰亭的竹荫,温热醉人的黄酒,胡兰成张爱玲含珠发光的城市……江南,又在千里之遥了。
我曾于蒙昧中度过二十余年,许多烦恼与激愤,如今看来都不值一提。人生如果真的是一段旅途,想必面对一些崇山峻岭,总要经过许多个忽明忽暗的隧道,像一些困惑的日子里一个个耳畔轰鸣、视野昏暗的昼夜。有一天我蓦然惊醒,发现如果尘世没有离别、遗憾、失去和绝望,我们就不能找到相遇、欣喜、拥有和希望的任何意义。这样一想,我的双臂就柔软了,放下无用的包袱,腾出两手,慷慨揽未知入怀。
江南其实一直都在,去了就不会晚,正如所有的远方和所爱。深情,难道不正是如此,无论严寒与凋零,斑驳与变迁,我来了,不改初心。草木不重要,建筑亦不重要。我们要去的地方,其实不过是自己的心里。我们想要看到的风景,亦不过是给自己心中的故事,找一个清晰一些的背景。
所以,江南怎会让我失望呢?人世亦不再会。我来了,许我热烈深情一回。
责任编辑 苍梧遥
第一次拈一枚雪白轻盈的蚕茧在掌心,初夏窗前,车水声中,梦回以后。捧住这新生的珍贵缠绵,不由得想起华夏土地上千百年来的浣纱、纺绣……甚至可以想象自己已经捧住了一整件羽衣霓裳。不过,笙歌还来不及,旋即就又痛到义山的相思与寸灰。
暮春田间,四处问访桑树何在的辛劳还在心头。想到胡兰成笔下有桑叶、竹笋和月光的浙东,忍不住又想到张爱玲去温州找他,远远地倚在舢板栏杆上望着将至的前方说:“因为他在那里,我感觉一整座温州城都像含珠一样闪闪发光。”再想到自幼吟诵着《江南春》与《桂枝香》的迦陵先生,漂泊海外大半生,以燃烛之热忱投入祖国古典诗词,为异族的学生们一再深情解释古老中国的“烟柳画桥”与“风帘翠幕”,自己却年逾古稀,才第一次有机会踏上宋词中熟稔了千千万万遍的江南。
迦陵先生说,词之美在于曲折幽微。曲折幽微,不正如人心吗?正如一枚春蚕之茧,一根细线,千回百转,看似严丝合缝层层内敛,却又并不是不可以在某一个恰当的时刻,以一种恰当的方式,牵出一个由头,抽丝、剥茧。梭如光阴,来来回回,心中的经纬,逐渐铺陈。往事若要挑出一匹来,染色成绢,请许我蘸一笔绿沈,以此浓重饱和春夏之色,寓意江南。
贰
要许多许多桑叶,才能被一只蚕,在暗室中耗尽终身,凝成一根漫长细丝。如同一个人,蒙昧仓皇置身尘世,要咀嚼亦或者狼狈吞咽多少内涵丰富的日子,疼着消化不良的胃,在许多许多个不眠的深夜中去反刍、辗转,才有可能在某一个黎明之前,抓住些许游丝般的答案。
要以一颗温暖的心,安放在一个不再消瘦的身体里,去江南。要在火车上看地图,密密麻麻的路线像迟钝已久的神经网路,每一个地名唤醒一个节点。——所有的远方都是别人过腻了的家门前,我懂得,不要真以为我会误会,这一路过去即将惊见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但,这并不重要。江南,它穿过一场漩涡一般令人涉足就注定淹没其中的文学史,早已不再是一个地理名词,而是这场历史中一个独一无二、美丽哀愁的意象。江南,是几句话他在几百年前留下了,几句话你在几百年后惊心了,这两者之间的一份深深懂得。
在明故宫的城墙下,用掌心一寸一寸摩挲过那些斑驳生苔的陶砖,辨析有些砖头上烧制的作坊商号和掌柜姓氏,怅然凝噎。我这么一伸手就贴近它们了,还可以随便拍上几张照片。可是,我心里明白,我与它们是隔着多少兴亡,人事离合的层层叠叠。看山看水纵然是好啊,可惜终究不如如此,装几段故事,千山万水找到历史的残迹,默默地坐下来,喝一口水,怀想。
中国的修史传统自古严谨,或许是面对悠悠苍天,亘古日月,祖先们自觉个体的生命实在太过短暂,便只好以一代又一代延续无尽的历史感来宽慰心怀。江月年年,长江流水,金陵果然是最宜怀古的。从两千多年以前卧薪尝胆的石头城,到一千七百多年以前浪花淘尽英雄的东吴建业,再到一千年前曾车如流水马如龙,雕栏玉砌又终不再的南唐……所以,病逝于斯地的临川先生,两度罢相之后,大约终于化激奋为沉郁,在某个萧瑟晚秋,于千里澄江似练的长江边,写下了“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的千古绝唱。当他离世,走进多少因他而改变过流向的历史长河之册页,历史本身自然不会停下脚步。1368年,洪武大帝赶走蒙古人,将大明帝国定都南京。但他的儿子永乐皇帝即位以后迁都北京,在北京城修筑了令友邦使者想要朝觐中国君主,不得不走得气喘吁吁方能遂愿的紫禁城。可惜,两百多年以后,李自成逼死了崇祯帝,清人鸠占鹊巢,坐上了太和殿的龙椅,建康城前朝故宫的宏伟壮丽,从此在历代的兵灾战火中分崩离析。彼黍离离,彼稷之苗,残存的宫殿柱础,四周野草蔓芜。
三百年前,曹雪芹在这座遗址之畔的某一座宅院里出生,学步学语。在那部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的著作里,他念念不忘让甑宝玉住在金陵。曹雪芹出生后不久,吴敬梓寓居秦淮,在《儒林外史》的市井生活里铺陈了清中叶江宁城的纷纷场景。又过了两百多年,余光中先生在南京出生,上小学。抗战爆发,他在战火中失去家园,随着母亲一路流亡到四川,再后来是异国他乡。回忆故乡他写到:“杏花。春雨。江南。六个方块字,或许那片土就在那里面”,他也记得养蚕:“在江南的泽国水乡,一大筐绿油油的桑叶被噬于千百头蚕,细细琐琐屑屑……”。
从曹雪芹到余光中,一回首,就是三百年。从李璟、李煜、冯延巳到余光中呢?竟然已经一千年!可是如果我望向书柜,我却可以看见他们相距很近,咫尺之间。文学的魅力在于,它可以从臃赘的人类历史中轻易就脱颖而出,略过时间与空间,略过尘世恩怨情仇,甚至略过作家本身,永恒成一颗一颗亮晶晶的星星,镶在不眠人的夜空里。正如此刻,它们纷纷静默地伫立在不同的城市里,不同大楼的不同房间,不一样的书柜里。兵荒马乱,只能毁灭王朝与宫殿,却消损不了文学。且人世悲欢,恰恰能让每一句穿越千年的诗与词,都带着作者的体温与心跳,眼泪和叹息甚至血泪,完整如初地抵达另外一个读者的心灵。
如果一条河、一座城,不曾被一颗丰盈易感的心灵低吟徘徊,它们纵然赏心悦目呵,终究只是无心的风景。但是寻常的阡陌,屋瓦人家的桃花,却可以因为几句诗,从万花丛中独树一帜,自西周一路热烈盛放到如今。春天来得比蜀中更晚的长江以南,就因为它是一晌贪欢的江南,是日出江花红似火的江南,它就值得被一个懂得的人所向往、流连忘返。
我们爱的,本非万物,仅仅是万物所承载的深情。
叁
如果江南只是一个朦胧意象,钟情于这个意象的人,难免分不清楚江苏与浙江,分不清楚那些近似的地名应该归属于哪个省份。我们只需要晓得,那里水气氤氲,遍地风流,那里有这两百年以来最耀眼的文人墨客,最传奇的才子佳人。
要确认过无数次,才讶然发现,原来王羲之、陆游、鲁迅和胡兰成,他们都是会稽山阴人。四川盆地的气候,每年最冷的时候只有一周,在冬至过后,摄氏六度左右。可是,想不到立春将近的浙东,湿冷阴霾超乎家乡的冬至时节,最冷的那天,我把本来用来换洗的两条打底裤和一条牛仔裤,合三为一穿到了一起。
难忘绍兴站灰蒙蒙的天空和一地的冷雨。我往手里呵气,暗自感叹,这真是酝酿《故乡》与《祝福》的最适宜天气。当年鲁迅先生从水路回家,大约也衣衫单薄,才忍不住回头在《故乡》里写下:“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阴冷寒湿带上一点文学氛围,意味也就与众不同了,我愉快地把不适视为了享受。再忆及张爱玲在《秧歌》和《异乡记》里浓墨重彩的描写寒冷,讲的正是旧年腊月到新年正月的两个月里,浙东乡下难耐的严寒,以至于新下乡的青年作家顾刚,没有火炉竟然冻得无法入睡。如此回味一番,不但安心享受起这份天气,简直还要庆幸自己准确地选择了这样一个恰当的时间来到江南。
拦一辆出租去鲁镇,听司机用浙江口音浓重的普通话热情介绍绍兴美酒与风物,不忘叮咛我们来回乘车事宜。汽车穿过大片并没有作物生长的田野,我望着车窗外赭赤色的泥土,一整颗心都被温暖。从兰亭回城里,与游客拼车,一路上全程收听一位当地阿姨与司机相互打趣,从最初的茫然到后来的明白,不禁莞尔。之前喝过的一点绍兴黄酒刚好上头,我一遍遍在心里默念他们咬字的音节,像用手指一粒粒摩挲过一串温润珠链。藉此,沈园带给我猝不及防的惆怅,才算渐渐平息。
肆
几年前在华清池,越往里走,《长恨歌》的句子在心头敲得越疼。红尘路窄,竟窄到一位曾呼风唤雨、四面来朝的君王,要亲手将心爱的女人推出门外。人在江湖,终究是如此无力、无助、无辜,而尴尬的存在。我的整个西安之行,从那一刻起,深深陷入“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心酸与迷惘。
而沈园来给我的沉痛,犹有过之。
南宋半壁江山,文人武将,莫不切盼收复失地,其中可歌可泣者,数不胜数。倒是放翁,一生执著,最后落得个“爱国诗人”的名声,让人潸然。是啊,稼轩、岳飞、陈亮、文天祥……他们亦曾以诗明志,留下千古名篇,可是他们不以“诗人”名世。他们亲身披甲上了战场,天命人事的博弈之间,他们一腔热血交付了所有,求仁得仁。可是陆游,他没有得到这样的机会,“江山不尽英雄恨,天意无私草木秋!”
陆游一生写过许多有关梦境的诗词,梦中他总是听见金戈铁马,剑鸣鞘中。四十九岁尚在壮年的陆游,任职蜀中念念不忘抗金:“逆胡未灭心未平,孤剑床头铿有声”,翌年他又叹息担忧:“国仇未报壮士老,匣中宝剑夜有声”。然而,漫长的二十六年过去了,壮志未酬,英雄终白头。七十六岁的陆游归老山阴,已倍感怆然:“万里关河孤枕梦,五更风雨四山秋。”
光阴不饶人,严相逼,我甚至有些以为,放翁能长寿至85岁,就是因为他不甘心,望眼欲穿有期待。要把他的诗词从年少意气风发,一路读到他年迈于时局无能为力,才会在面对《示儿》时,心如刀绞,泪流满面。再回想他在47岁时,于蜀中路过剑门山避雨,曾不甘心地自嘲“此身合是诗人未”?想不到最后,他真是个诗人,修饰语还是“爱国”。
陆游一生所倾情者,无非收复国土和怀念旧爱。多年以前我就曾想,如果我要以陆游的复国理想写一篇文章,题目就该叫做《铁马冰河入梦来》。很感念沈园的管理者,重门之后,曲苑尽头,他们在陆游纪念堂前,安放了两座相向的雕塑,一座是陆游像,另外一座,正是一匹铁马。
当然,千古伤心之地沈园,承载的并不是陆游的复国理想。
1144年,二十岁才华横溢的陆游迎娶唐婉,夫妇二人情投意合,如胶似漆。可是陆游的母亲不喜欢功名未成的儿子被儿女私情过于耽搁,渐渐不喜欢唐婉。他们婚后不足三年,陆游就被迫休妻,佳偶无奈分离。1147年,陆游娶了第二任妻子王氏,唐婉也再嫁给当地另一位名士赵士程。如果不能相濡以沫,相忘于江湖也是很好的。可惜在1155年的春天,31岁的陆游与唐婉,却在沈园不期而遇。一别经年的故人,发乎情、止乎礼的分一瓿薄酒,这些年的心事有口难言。唐婉离开之后,作为诗人的陆游,不耐感慨,挥笔在沈园的墙头上写下一阕《钗头凤》,怨世事弄人,叹离情难寄。
春寒的绍兴,沈园里的植物还残余着严冬的凋零。我着急想去看那面刻着《钗头凤》的墙头,已经穿过了两道园门。没料到第二道门内,流水蜿蜒,九曲回肠。我踏上石桥,望脚下流水,一刹那就痛彻了陆游在75岁高龄之际写下的那两句诗:“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
如果陆游与唐婉的故事,以第一首《钗头凤》戛然而止,我想,中国文学史上,不会出现陆游后来以沈园和唐婉为主题的那么多比《钗头凤》更深情悱恻的诗歌。如果爱情的难题,只在于有情人不能长相厮守,以时间之灵,倒还可以消磨一切心头不平。可是,如果在一场不能厮守的爱情里,一个人竟然为另外一个人付出了生命,时间于生者,当然就不可能再是抚慰的灵药,而变成历久弥新的折磨。
悲剧逐渐走向高潮,唐婉于惊鸿照影的翌年再度游历沈园,惊见墙上陆游所题之词,“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邑鲛绡透。”前尘往事,排山倒海向她袭来。哀愁恍惚中,这位情深义重的女子泣血和了另一首《钗头凤》之后,竟然在当年秋天郁郁而终!
唐婉因为自己而早逝,让陆游陷入无尽感动与愧疚之中。他一生的情感世界,从此被这位用整个生命来爱过他的女人,深深萦绕,至死方休。1188年,64岁的陆游从严州任满归山阴,沈园依旧,前尘隔海,他写下第一首怀人之诗:“唤回四十三年梦,灯暗无人说断肠。” 那一年,距离他和唐婉初婚,已过去四十三年。年逾花甲的陆游在宦海中又经几次起复,直到73岁才彻底罢官回乡。回到山阴之后,他在沈园墙下哀叹:“坏壁醉题尘漠漠,断云幽梦事茫茫。”故乡生活使他常近沈园,旧事旧痛无以回避,终于在两年之后,75岁的陆游写下被陈衍在《宋诗精华录》里称为“绝等伤心之诗”的《沈园二首》:“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81岁,白发苍苍的陆游“路近城南已怕行,沈家园里更伤情”,因为他感慨“玉骨久沉泉下土,墨痕犹锁壁间尘。”82岁,残年的陆游踱步到沈园门口,发现园门被锁,担心当年的《钗头凤》已被灰尘和青苔浸蚀:“尘渍苔侵数行墨,尔来谁为拂土墙。”85岁,江南草长莺飞的春日,风中之烛的陆游最后一次来到沈园,就像同时为子孙写下《示儿》一样,他为自己缠绵一生的爱情写下绝笔:“沈家园里花如锦,半是当年识放翁。也信美人终做土,不堪幽梦太匆匆!”
我总是容易被深情执著的心灵所感动,无论他的燃烧是为了理想还是爱情,陆游竟是兼而有之,春蚕至死,蜡炬成灰。我并非不钦佩智慧的云淡风轻,可是我觉得,真的淡泊,背后一定是情深的汪洋大海。渡得过来,才看得明白。
伍
灯下。窗前。
南京的梧桐,兰亭的竹荫,温热醉人的黄酒,胡兰成张爱玲含珠发光的城市……江南,又在千里之遥了。
我曾于蒙昧中度过二十余年,许多烦恼与激愤,如今看来都不值一提。人生如果真的是一段旅途,想必面对一些崇山峻岭,总要经过许多个忽明忽暗的隧道,像一些困惑的日子里一个个耳畔轰鸣、视野昏暗的昼夜。有一天我蓦然惊醒,发现如果尘世没有离别、遗憾、失去和绝望,我们就不能找到相遇、欣喜、拥有和希望的任何意义。这样一想,我的双臂就柔软了,放下无用的包袱,腾出两手,慷慨揽未知入怀。
江南其实一直都在,去了就不会晚,正如所有的远方和所爱。深情,难道不正是如此,无论严寒与凋零,斑驳与变迁,我来了,不改初心。草木不重要,建筑亦不重要。我们要去的地方,其实不过是自己的心里。我们想要看到的风景,亦不过是给自己心中的故事,找一个清晰一些的背景。
所以,江南怎会让我失望呢?人世亦不再会。我来了,许我热烈深情一回。
责任编辑 苍梧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