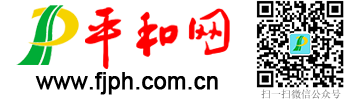那一棵棕树
原产中国的棕树很常见,树势挺拔、叶色葱茏的棕树在庭院、花坛、屋角等等都可以见到它的身影。或许是太过常见,尽管是常绿的乔木,动辄十多米高的身姿并没有吸引太多关注的目光,所谓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用在棕树的身上好像也颇为贴切。
记得一棵棕树是从孩童的记忆开始。这一棵棕树生长在崎岭浮坪老家的屋角,当年祖父为何在那个地方种下这么一棵棕树已经无从询问,但那棵棕树就这么机缘凑巧地在我的视线中存在。棕树有七八米高,圆柱形的主干直通通地向上生长,没有什么分枝,也不会像柳树来个曲折的造型,粗糙的枝干诉说生长过程的艰辛,只有在枝干的顶端簇生着硕大的叶片,掌状分裂成狭长坚硬的裂片。在树干接近叶片的地方,层层残存不脱落的老叶柄基部,被暗棕色的叶鞘纤维包裹着。每到五月,棕树就会盛开淡黄色的花,花排列成圆锥形,不过我们对那些花不感兴趣,我们感兴趣的是11月开始成熟的棕果。棕果小小的,挨挨挤挤地生长在那儿,就像放学时蜂拥而出的学生,没有什么秩序。这些如今多为观赏用的棕果,在那缺少水果的年代成为我们的渴望,每每棕果成熟的时候,我们就拿刀劈下一串,吃得嘴唇发黑、口腔发涩,张开口都很困难,好像被什么粘住一样,招来大人的昵骂。
无聊的时候,拿刀砍下一片棕叶,举着长长的叶柄,玩得兴趣盎然。或者把叶片细细地撕成丝,拂动之时,宛如武林高手的拂尘,轻轻一挥刀光剑影。更为实用的是驱赶蚊子,夏天临睡之时,在蚊帐里挥动一番,足以让蚊子落荒而逃。偶尔大人也作为鞭打调皮孩子的工具,蹦跶哭喊的时候我们只记得疼,却无暇去后悔当初怎么会去做出这样的工具惩罚自己,善于总结那是长大以后的事情,所以大人永远比孩子活得累。农忙的时候,姐姐把棕叶砍回来,连叶柄也不留,细细地撕成丝,不过那不是为了玩,而是第二天拔秧苗的时候扎秧,棕叶已经成为农民的农具了。
棕树的价值更多的是体现在那些棕丝上。农闲的时候,祖父会带着刀,爬上棕树,沿老叶柄的基部环割一圈,把老叶柄连同包裹的叶鞘剥下来,在大锅里用开水煮过,拿到小河里,用石头压住,让清清的河水浸泡。几天之后,捞出来,用石头在叶柄上细细地砸过,继续压到河水里浸泡。祖父的劳作就是为了让叶鞘上的果胶和棕丝分离。如此几遍过后,爷爷就把棕丝和叶柄分离开来了,在阳光下晒干。
这些棕丝或者卖给走村串巷的货郎,或者爷爷把它搓成棕绳捆扎东西,主要还是用来编织蓑衣。在以前的岁月里,蓑衣是重要的农具,要变天的日子,有经验的农人总是带上蓑衣斗笠。风雨袭来的时刻,戴上斗笠,穿上蓑衣,就可以把风雨遮挡在距离之外。如果风雨很急,走到田坎,把蓑衣的一面迎着风雨,不必要什么动员或者命令,蓑衣静默地承担起迎击风雨的责任。仅仅是雨,那就无需走动,穿上蓑衣站在水田之中就足以让雨不再袭击身体,也是短暂的休息。也许在诗人眼里,穿着蓑衣的农人站在天地之间是道风景,但农人只知道蓑衣的温暖可以削弱雨水带来的凉意。等雨小了一点,穿着蓑衣的农人就忙碌开了,哈腰干活,蓑衣就是一道屏障,遮蔽了干活的农人,避免了风雨的侵蚀,也没有误了农事农时。暴雨突然袭击的时候,我经常干的活就是给在地里干活的父兄送斗笠、蓑衣。山路上总是急匆匆地奔走着我这样半大不小的孩子,手中无一例外地拎着蓑衣。
蓑衣大多是农人请匠人自编的。冬天农闲的时候,有匠人走村串户编蓑衣。农人平时把自家房前屋角棕树的棕叶采割浸泡抽丝,这时候搬出来交给匠人就等着拿到新蓑衣了。匠人晚上也加班,寒冷的冬夜,匠人在昏黄的灯光下把棕丝铺好,用个小小的木头锤子锤实,然后用棕丝搓成的细绳子连缀,那绳子拉动丝拉丝拉的声音很是悦耳。到了10点之后,主人会把夜宵端出来,请匠人吃夜宵,我们也可以沾光吃上一些。我对童年编蓑衣的记忆很多因素就是因为这碗夜宵,尽管要么是红糖糯米粥,要么是一碗米粉或者面条,或者干脆就是就咸菜吃碗白米粥。但在那个年代,这些却是诱惑力极大的美味佳肴。
小的时候,以为蓑衣总是温情脉脉的,后来穿上蓑衣干活才知道,蓑衣在雨水冲浸之后沉重无比,那细细的绳子会勒得肩膀生疼。只是我们对这份沉重无法拒绝,就像我们无法拒绝许多苦难一样。我们无法一逢雨天就在家休息,我们就得选择带上蓑衣上路,那份沉重就是生存的艰辛。蓑衣还和生命的存失藕断丝连。记得一年夏天,有个村支部书记在台风天带着村民清理山体滑坡,谁知道清理过程中继续滑坡的山体把村书记推到路下的山涧之中。山涧洪水湍急,身穿蓑衣的村书记无法甩脱浸水后沉重无比的蓑衣,不幸遇难。蓑衣成为其子女的黑色记忆,不时搅痛他们的心灵。
蓑衣的沉重和它刺人皮肤的细丝,让许多农人后来选择了塑料薄膜,蓑衣逐渐退出。塑料薄膜是简单易带,但轻松之后的轻飘飘许多时候无法抵御风雨,老一辈的农人就无限怀念蓑衣,留下许多感慨。
由蓑衣想起了“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这句诗,眼前恍然出现天地之间平静忘我的智者形象,那份超脱让许多尘世的纷扰纷纷落地,成为不值言说的尘埃。蓑衣在这里,抵御的不仅仅是风雪,更是内心的一道屏障,把自己包裹起来,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但更喜欢“一蓑风雨任平生”这句话,蓑衣在这里成为勇者的披风,跟随主人傲立尘世,无需选择地点,也不必隐居或者躲避,自己活成一道风景,任风雨侵蚀,我自岿然不动。这样文化的意象刷地和孩提时代看到的忙碌农人联系起来,发现了他们本质的惊人一致:他们做自己的事情,不屈服于外界的风雨。蓑衣就和武士的盾、剑客的剑一样,让许多人有了勇气。
蓑衣日渐少了,少了的蓑衣挂在老家的墙上,和老屋逐渐成为历史,吸引了不少游客的目光,甚至引发了一叠惊叹。有游客把蓑衣买回去当成装饰,或者穿着蓑衣照相,满足自己的某种新奇。蓑衣无言,但这样的喧嚣已经不是蓑衣农耕苦作的原汁原味,历史不是装饰品,蓑衣也不是。蓑衣,注定渐行渐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