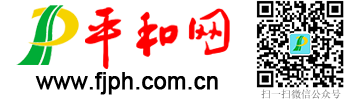陪你看太阳
编辑按:
陪你看太阳
——得荣纪行
我把情歌化作一朵浪
沿着你的山谷自由流淌
自由的心像山风穿行
给我的思恋长一双翅膀
谁的遥望给我一道光
照得我的飞翔天地宽广
我要回到你身旁,陪你看太阳
看那高原的阳光映红你脸庞
——罗桑金玛《陪你看太阳》
“这是一首唱给母亲的歌”。那个藏族小伙子一只手扶着椅背,一只手随着车身的抖动自然晃动。“雪狼组合的成员之一,现在我们得荣接待办工作。”有人介绍说。小伙子唱起来,旋律比较熟悉,对,就是那首《慈母》。“你是光辉的太阳、生命的月亮”。高亢宽阔。那个小伙子曾经在各种舞台演出,灯光华丽、万众瞩目,或者天空地阔、清风流淌。在狭小的车厢里,为疲惫的他乡来客唱歌,应该也不是第一次。在海拔三千三百米的高处,在深夜,在歌颂母亲的清唱里,柔软的哈达滑过冰冷的脸颊。一些光芒让夜色豁然开朗。
白墙后的酒吧依然灯火通明。客人已经不多,靠墙而坐,像漂浮的阴影。几盏灯将舞台照得很亮。一面小鼓,一把吉他,一只麦克风架子,一条长凳。那么多人寻梦香格里拉,人声鼎沸之后,留下了空。喝酒。主人说。身板高大结实,两鬓华发参差。喝酒!主人的声音淳厚而略显苍凉,目光温和阔达。喝酒。大家说。橘黄的灯光滑动微尘,人声忽远忽近。一个自成一体的世界,自己组成的世界,却分明隐藏了深深的秘密。
新的一天开始了。热水让我从酒吧的情景中醒过来。快中秋了。突然想起的却是关于春的那首宋词。“别来春半,触目柔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 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 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我信笔写下这样的句子:“有些风景的美在于自己根本无法理解。就像一个梦,明明经历了,却在睁眼之间遗忘或者失去。牵扯自己心灵的,始终是季节的反照。不归如何?归又如何?不论是春草,还是秋叶,不论是山水,还是星辰,都不是寄托和安慰。渐行渐远,一切却紧紧包裹。”
还有一百四十公里到得荣县,我们在路上。雨细碎密集。一些牦牛的黑点散开在枯黄和淡绿的田野上。风无遮挡地吹,一片片青稞地像晃动的毯子。转过山坳,一大片水忽然就到了眼前。一个叫的“纳帕海”高原湖泊。“纳帕海”,藏语原意就是“山那边的湖泊”。疯长的青草一直向水里伸展,大大小小的沼泽神情肃穆。一些木头房子建在水面上,大多残缺破旧,有一种荒凉的静谧。水面远远的伸展,似乎没有尽头,却还看得见更远处的山。
路分开连绵的雾。海拔已经有四千多米。一边是草木稀疏、碎石嶙嶙的山坡,一边是不辨深浅、翻腾沉浮的浓雾。下面是峡谷。几百米、上千米深的峡谷里有些什么?我闭上眼睛,呼吸有些凝滞,不知道是因为稀薄的空气还是内心的恐惧。我看见大片大片金黄的花朵在岩石上绽放,在密密的松树枝头炸开,在黑色的屋顶摇晃,甚至在青稞地里流淌。流成一条河。那些巨大的石头浮在河面,像一条条没有航向的船。最近总是梦见金黄的花朵,那些花朵在梦境里随处可见,是心灵隐喻?是人际折射?在车的颠簸中醒来,我揉了揉太阳穴,不再理会那些疑问。
雾在消散,雨却紧紧追赶而来。藏青色的山簇拥着,堆垒着,伸展着,慢慢接近天空。山山横断,断岸千尺。这里被称作“金沙江第一弯”。我看过一张这里晴天的照片。水清澈,山苍翠,阳光明媚,软软的白云向碧蓝的天空伸展。一些深红的光晕在山间滑动,显出无边的神秘与神圣来。而此时雨密风紧,众山之间,一山孤突,金沙江像一条深黄的带子,漫不经心地环系山脚。
下山,一个叫“瓦卡”的村庄。“瓦卡”意为“渡口”。一道钢架桥横跨金沙江。浊流翻滚,一泻千里。钢架桥在风里发出尖利的啸叫,水却静默无声。这是茶马古道进入金沙江的第一道渡口。在此前的一千多年里,一代一代商人沿着金沙江河谷穿越横断山区,走过青藏高原,穿过喜马拉雅山口,最后到达印度、尼泊尔。在云南、四川、西藏的山野,在纵横交错的道路上,在汉、藏、纳西各族商人的行李中,在拉萨、加尔各答或者加德满都的集市上,在战争与和平之间,普洱茶饼成为人类历史的一种象征,承载生生不息的命运链条,以及对生命本身的珍惜或者暴殄、追求或者抛弃。
于人而言,每一段历史都赋予一个地域方不同的意义,而那个地域,只要不发生沧海桑田的变迁,本身存在的历史往往比它所承载的人类历史更漫长、更独立、更有延续性。所以作为渡口的瓦卡不是有悠久历史的村落,并不令人意外。多年来,人们习惯住在高处,尽管高山上生存条件非常恶劣,但也许高处更加接近神灵。让人们从高山迁徙到河谷定居,也是近年的事情。一片一片玉米地,玉米地之间是参差隐现的葡萄园,玉米地和葡萄园之外,有青葱的菜园,有挂着累累果实的藏梨和柑橘树。色彩艳丽的藏族民居就在田地边沿、果树合围之中。
这是得荣县庚子乡政府所在地,也是进入得荣的第一站。一粒小小赤霞珠入口,酸涩深刻宽广,清甜细微飘渺,一下子让人品出生活的味道。而藏梨有一种纯净的甜,干净,安宁,柔和,平缓,慢慢渗透心脾,心灵为之一空,便多了些宗教色彩。雨停风住。丝丝缕缕的阳光将树叶照得透亮,随处可见的白塔散发出明净的光芒,经幡飘动如蝶,一纸天空停在高处。援藏两个月的年轻同事脸上已经有了明显的“高原红”, 他正在放弃一个休闲城市养尊处优的生活习惯,努力接受偏僻、陌生和艰苦。而最不堪的是孤单,是深夜整座大楼只有他一个人的空与寂寞。他不停地说话,他说话时的欣喜像一道亮光在空气中摇曳。
庚子乡党委书记,一个干练的藏族女子,为她的政绩感到自豪,对未来充满信心。生活的意义其实并不神秘,幸福的密码往往就是生活的快乐和内心的安宁,有追求就有快乐,有皈依就有安宁。明天总是美好的。我对他们心怀敬意。人,人群,总是在进退之间,传承延续。祖先创造了辉煌的文明,曾经造就一个时代最好最风光的生活方式,他们以为那是理所当然的永远。然而自然灾害、战争、瘟疫在最短的时间以最简单的方式毁灭一切。又一代人只好后退,退回荒野,退回最初,茹毛饮血,繁衍后代,积累财富,养育文明,直到下一个轮回。
因为“一夫多妻制”,“金沙江河谷地带”曾经作为一种独特的人类学域名存在。很多专家在这里走访研究,探寻这种习俗的源流,也做出了多种解读。任何一种习俗,都取决于生存环境的安排,都是生存环境在人类心灵的折射,有的随着生存环境的改变而改变,有的融入人类血脉固执地传承下去。比如“一夫多妻制”,这种原始群婚制的遗存,契合了恶劣自然条件下家族繁衍、财富积累的需求,至今都没有被完全摈弃。女书记很认真地告诉我们,牧民集中居住,条件改善了,这种情况基本上不存在了。
午后,沿“金沙江第一湾”往北,走向得荣县城。金沙江就在眼前,泥浪滚涌,水声轰鸣,水雾蒸腾。江心往往有巨石,浪涌消失无踪,浪过突兀而出。江面狭窄,江水狠狠地冲击两岸,大浪轰然撞向两岸的岩石,撞成弧形的水幕垂落江面。“中国第一大河”上游的狂暴和急促此时展露无遗。这里真有那张图片上江青水碧的时候吗?突然想起“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的句子来,耳边就有了鸟鸣声声,但始终没有看见鸟飞过。
“得荣”也称“得隆”,意为“峡谷之地”,是康巴藏区的门户,西南与云南中甸、德钦接壤,北与四川巴塘和乡城紧紧相连,东北部与稻城毗邻。曾是巴塘土司的领地,民国时期属西康省管辖;解放初年成立人民政府,隶属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横断山系北段,群山耸峙,峡谷纵横,嘎金雪山海拔近五千米,其余诸峰多在四千米以上,山岭和峡谷落差高达两、三千米。得荣县就在这些山岭峡谷间,低纬度,高海拔,大落差,气候干燥,阳光充足,因而也被称为“扎西尼玛龙巴”,即“吉祥太阳谷”。
时近黄昏,县城街道依然拥挤。大大小小的车辆飞鸟归巢般涌向县城,长约四、五百米的县城主街道两边满满地停了两排,没有地方停放的还在往前缓慢移动。许多人穿行在车流之间。匆匆的,应该是机关单位的工作人员,下班了,急急忙忙回家。身着藏族服装,带着孩子的,应该是县城附近的居民,慢慢走过。行走更缓慢的,是穿着僧衣的人,看不出他们行走的方向。定曲河穿过县城,铁青色的水面涌动点点光斑,水声哗然。
主人极尽地主之谊。在热烈张扬充满宗教意味的祝酒歌里,衣香鬓影,觥筹交错。我们此行,当然有很多工作任务,我们都希望在那片还很陌生的土地上做出真正的业绩。主人的热情让人无法拒绝,大家很快入乡随俗。因为感冒,我头痛欲裂,很快仓皇退席,回房间和衣而卧。
我看见大片大片绿跌落在褐色土地上,一蓬蓬花开得姹紫嫣红;我看见一群人席地而坐,大地上响起宽广的梵唱;我看见一座座佛像庄严排列,檀香缭绕一笼笼烟雾;我看见无边的洪水倾泻而来,冰凉的感觉瞬间将我淹没……醒来时汗湿衣被,一种迟钝的酸疼深入肌骨。窗外已经有亮光轻盈地飘进来,定曲河哗哗水声一如昨晚。服了感冒药,换了睡衣,却再也无法入睡,只好起身出门。
清晨的天光飘洒在定曲河上,湍急的河水清亮新鲜,水声明朗轻快。青石垒成的河堤上,苔藓依旧葱绿,潮湿的味道在石头上蔓延。一个红衣僧人在河边人行道上慢慢走来,没有感觉出他的移动,他已经近在眼前。是很年轻的僧人,宽阔的额头,浓密的眉毛,黝黑的脸上有明亮的眼睛和干净的红晕。很快他飘过我身边,越去越远,不见了踪迹,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一群小孩突然跑过,一脸灿烂的笑转瞬即逝,笑声却在空气中久久飘荡。
太阳谷广场的标志性雕塑上,载歌载舞的姑娘和小伙子笑颜如花。我猜想他们应该代表了太阳和月亮吧,那是当地藏民内心崇高信仰的载体。广场上一片空阔,人群活动留下的风尘已经被晨风吹走,只有几个饮料瓶子心有不甘地留在角落。石碑上用藏汉两种文字刻着《太阳谷赋》,应该是这里的一种文化标志吧。因为对当地文化的陌生,而那些文字又在古奥与白话之间跌宕起伏,尽管全文诵读,却难解其意,只好抱憾离开。广场边沿坐着两个老人,一动不动,仿佛一直在那里,默默地看天空。我从他们身边走过,走到河堤附近,就看到定曲河的雪浪花一片片开放。回过头,老人已经消失了踪影。
作为对应的援建单位,我们有四十九名干部在得荣县开展为期两年的援建工作。他们在县政府、县级经济部门、一些乡镇担任副职,主要任务是找资金、建项目,加快当地经济发展。两年内,他们需要融入藏族群众,在尊重藏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的基础上,逐渐改善他们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增强藏区的发展能力。资金和科技并不难以送达,难的是民族心理的真正沟通与充分融合。尽管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诸多学科对此都有种种论述,也给出了多种方法,但是在实践中的成效却差强人意。
历史上,汉族统治区开发或援助少数民族区域的例子并不鲜见,比如秦汉之于南越、蜀之于彝区、唐之于吐蕃、两宋之于云南,直至清代的“改土归流”。这些开发和援助,有驻军屯田、移民开荒,有册封藩王、派官员管制,也有特殊的“和亲”“为一家”。但不论哪种方法,都以暴力作后盾、以少数民族“归化”为目标,为的是“千秋万世、一统山河”。从这个角度比较,如今的援藏显然是一种全新的工作,没有历史经验可借鉴,没有现成的方法去遵循,一切都需要智慧重新创造。
所以,尽管有诸多文件明确规定他们去干什么、怎么干,但是援藏干部一进入藏区遇到的最棘手的问题也许还是“干什么、怎么干”。他们需要放弃早已熟悉的生活方式,改变按部就班的工作习惯,努力寻找新的切入点,以藏族群众可以接受的方式开展援建工作。他们必须改变“投桃报李”的价值观,对援建工作倾注真情,以真正的热爱去接受面临的一切,然后奉献自己的力量。每个人都有梦想,我相信,他们绝大多数人是怀抱了梦想进入藏区的,他们憧憬着两年之后更加丰满的现实。
阳光明丽清澈,风慢慢滑动。沿定曲河北上。峡谷两边依旧一片葱绿,褪色的经幡在河上飘拂。万物安宁。一片叶子凋落,在阳光里撞击出金属的声音。车在一个老人身边停下来,同行的县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局长阿青和她大声说话。老人戴着帽子,稀疏的白发在帽子外面轻轻飘,一脸浅浅的笑,目光柔和安静。我想起那首《慈母》里母亲的形象——她正是阿青的母亲。我不知道她们用藏语交谈了些什么,但她们的笑容让我莫名地感动。那笑容,无比熟悉,又显得陌生,轻盈地进入心底,又仿佛本来就是从心底里飘出来的。
天空忽然很高,那一抹浅蓝深不见底。山峰峻拔高耸,灰白的岩石堆积成山体,岩石的锋刃历历可见。绿点点飘洒,仿佛随时都可以随风飞走。太阳就在眼前,多么清晰的太阳啊,须发毕现,纤毫分明,触手可及。忽然想起一个本土歌手的吟唱,“谁的遥望,给我一道光,照得我的飞翔天地宽广”, 一切以一种最纯粹、最质朴的方式呈现,所有心灵的震颤源于太阳,归于太阳。
峡谷里的平地上有一处牧民定居点。一片红顶白墙的房屋基本建成,房屋之间的水泥路面平整光滑。近处山梁上,有颓圮的土墙,看得出是废弃的房屋,不知什么时候、什么人居住过。走过那些房屋,更低的谷地里,卵石之间,一株不知名的阔叶草本植物鲜红的果实格外耀眼。密匝匝的果实挤成一团,形成孤单单的一串挂在宽阔的叶子下面。圆圆的果子形似我们在瓦卡看到的赤霞珠,却非常坚硬,表面上覆盖着一层蜡质,没有葡萄的柔软和水分。我想采下来带回城市,作为此行的纪念。同行的同事坚决阻止,于是作罢。慢慢走开。回头,一眼就看到那渐渐变小的红,心里突然一疼,然后为自己鲁莽的占有欲羞愧不已。
阿青决定另走一条路,让我们看看雪山风景。正是这个决定,让我们第一次体会泥泞地带行车的艰辛。看似平整的泥地,留下了那么多车辙,我们以为那一定是坦途。实际情况是,车一下子陷在了泥泞中间,进退无据。我们下车,在灌木丛生的路边和阿青聊天。阿青身体健壮,神情平和,目光明亮,一身藏族女装更让她显出干练和雍容。和我们说话的时候,总是望着远处,语调平静却给人以充分的想象力。
她的讲述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藏民的生育观念。因为对神的信仰,藏民对自己都赋予了神的担当。如果母子平安,那是神的恩赐。如果母殁子生,那是因为母亲的责任和价值就只是送子到人世,孩子出生,母亲即追随神祗离去。如果母子俱殁,那也是神的旨意。实际上,自丛林时代以来,人类对自身繁衍的渴求往往炽热、坦白而且无奈。生死皆神圣,所以要听从神的决定。从医学角度讲,恶劣的条件显然严重影响人的繁衍。但也正是恶劣的条件,赋予了这个民族坚韧、强悍、忠于信仰、敢于担当的天性,锻造了一种难得的人性美。
晚上,我们见到了四十九名援藏干部的大部分人。一名同事在最边远的曲雅贡乡工作,早上出发,到我们县城我们聚会的地方已经晚上八点。按照惯例,大伙儿拿出一个小水桶大小的茶缸,给他倒上满满一大茶缸子啤酒。他没有推辞,双手捧起酒狠狠喝了一大口,在大伙儿的欢呼声里傻傻地笑。大家什么都不说,端起酒杯一饮而尽,脸上的高原红和干干净净的笑,恰如晃动着的太阳光斑。
“金树枝啊,请绽开你那鲜艳的花朵;银树枝啊,别弹错你那动听的曲调;玉树枝啊,别掉落你那翠绿的叶子;远方来的客人啊,请别拒绝我的挽留……”耳边突然响起据说是为迎接文成公主的到来而演唱的“学羌”歌调,与定曲河的水声相应和。我知道那又是我酒后的幻听,是对大家兴高采烈的祝酒声的内心回应。但我却无法不希望这样的歌声在寂静的山谷里真的响起,希望太阳谷广场此时出现花枝招展的人群和曼妙的舞姿,希望一切被赋予生命和灵魂的事物此刻都翩翩起舞,将所有美好的梦想变成现实。
离开得荣的路上,我终于看到先后接纳了玛伊河和硕曲河的定曲河,在三道绝壁之间汇入金沙江。河流交汇处,清澈的河流像是被硬生生切断,代之以浊流激浪。那里的金沙江奔腾咆哮,显出吞吐一切的王者风范。送我们离开的两名工作人员说,你们遗憾啊,只顾工作去了,没有看到翁甲神山,那里珍藏着开启藏区一百零八处圣地门户金钥匙啊;没有看看玛伊河峡谷、莫木沟和下拥,那可是人间仙境啊;没有去香火鼎盛的龙绒寺,那真是有求必应的神灵啊……
我想,我的同事们一定会看到,那时,他们的梦想也许就实现了。
然而我什么时候能再次踏上这片山水?“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这样的句子此刻显得苍白。那位叫罗桑金玛的藏族歌手在高声唱:“我要回到,回到你身旁,陪你看太阳,看那高原的阳光,映红你脸庞……”
责任编辑 苍梧遥
——得荣纪行
我把情歌化作一朵浪
沿着你的山谷自由流淌
自由的心像山风穿行
给我的思恋长一双翅膀
谁的遥望给我一道光
照得我的飞翔天地宽广
我要回到你身旁,陪你看太阳
看那高原的阳光映红你脸庞
——罗桑金玛《陪你看太阳》
“这是一首唱给母亲的歌”。那个藏族小伙子一只手扶着椅背,一只手随着车身的抖动自然晃动。“雪狼组合的成员之一,现在我们得荣接待办工作。”有人介绍说。小伙子唱起来,旋律比较熟悉,对,就是那首《慈母》。“你是光辉的太阳、生命的月亮”。高亢宽阔。那个小伙子曾经在各种舞台演出,灯光华丽、万众瞩目,或者天空地阔、清风流淌。在狭小的车厢里,为疲惫的他乡来客唱歌,应该也不是第一次。在海拔三千三百米的高处,在深夜,在歌颂母亲的清唱里,柔软的哈达滑过冰冷的脸颊。一些光芒让夜色豁然开朗。
白墙后的酒吧依然灯火通明。客人已经不多,靠墙而坐,像漂浮的阴影。几盏灯将舞台照得很亮。一面小鼓,一把吉他,一只麦克风架子,一条长凳。那么多人寻梦香格里拉,人声鼎沸之后,留下了空。喝酒。主人说。身板高大结实,两鬓华发参差。喝酒!主人的声音淳厚而略显苍凉,目光温和阔达。喝酒。大家说。橘黄的灯光滑动微尘,人声忽远忽近。一个自成一体的世界,自己组成的世界,却分明隐藏了深深的秘密。
新的一天开始了。热水让我从酒吧的情景中醒过来。快中秋了。突然想起的却是关于春的那首宋词。“别来春半,触目柔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 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 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我信笔写下这样的句子:“有些风景的美在于自己根本无法理解。就像一个梦,明明经历了,却在睁眼之间遗忘或者失去。牵扯自己心灵的,始终是季节的反照。不归如何?归又如何?不论是春草,还是秋叶,不论是山水,还是星辰,都不是寄托和安慰。渐行渐远,一切却紧紧包裹。”
还有一百四十公里到得荣县,我们在路上。雨细碎密集。一些牦牛的黑点散开在枯黄和淡绿的田野上。风无遮挡地吹,一片片青稞地像晃动的毯子。转过山坳,一大片水忽然就到了眼前。一个叫的“纳帕海”高原湖泊。“纳帕海”,藏语原意就是“山那边的湖泊”。疯长的青草一直向水里伸展,大大小小的沼泽神情肃穆。一些木头房子建在水面上,大多残缺破旧,有一种荒凉的静谧。水面远远的伸展,似乎没有尽头,却还看得见更远处的山。
路分开连绵的雾。海拔已经有四千多米。一边是草木稀疏、碎石嶙嶙的山坡,一边是不辨深浅、翻腾沉浮的浓雾。下面是峡谷。几百米、上千米深的峡谷里有些什么?我闭上眼睛,呼吸有些凝滞,不知道是因为稀薄的空气还是内心的恐惧。我看见大片大片金黄的花朵在岩石上绽放,在密密的松树枝头炸开,在黑色的屋顶摇晃,甚至在青稞地里流淌。流成一条河。那些巨大的石头浮在河面,像一条条没有航向的船。最近总是梦见金黄的花朵,那些花朵在梦境里随处可见,是心灵隐喻?是人际折射?在车的颠簸中醒来,我揉了揉太阳穴,不再理会那些疑问。
雾在消散,雨却紧紧追赶而来。藏青色的山簇拥着,堆垒着,伸展着,慢慢接近天空。山山横断,断岸千尺。这里被称作“金沙江第一弯”。我看过一张这里晴天的照片。水清澈,山苍翠,阳光明媚,软软的白云向碧蓝的天空伸展。一些深红的光晕在山间滑动,显出无边的神秘与神圣来。而此时雨密风紧,众山之间,一山孤突,金沙江像一条深黄的带子,漫不经心地环系山脚。
下山,一个叫“瓦卡”的村庄。“瓦卡”意为“渡口”。一道钢架桥横跨金沙江。浊流翻滚,一泻千里。钢架桥在风里发出尖利的啸叫,水却静默无声。这是茶马古道进入金沙江的第一道渡口。在此前的一千多年里,一代一代商人沿着金沙江河谷穿越横断山区,走过青藏高原,穿过喜马拉雅山口,最后到达印度、尼泊尔。在云南、四川、西藏的山野,在纵横交错的道路上,在汉、藏、纳西各族商人的行李中,在拉萨、加尔各答或者加德满都的集市上,在战争与和平之间,普洱茶饼成为人类历史的一种象征,承载生生不息的命运链条,以及对生命本身的珍惜或者暴殄、追求或者抛弃。
于人而言,每一段历史都赋予一个地域方不同的意义,而那个地域,只要不发生沧海桑田的变迁,本身存在的历史往往比它所承载的人类历史更漫长、更独立、更有延续性。所以作为渡口的瓦卡不是有悠久历史的村落,并不令人意外。多年来,人们习惯住在高处,尽管高山上生存条件非常恶劣,但也许高处更加接近神灵。让人们从高山迁徙到河谷定居,也是近年的事情。一片一片玉米地,玉米地之间是参差隐现的葡萄园,玉米地和葡萄园之外,有青葱的菜园,有挂着累累果实的藏梨和柑橘树。色彩艳丽的藏族民居就在田地边沿、果树合围之中。
这是得荣县庚子乡政府所在地,也是进入得荣的第一站。一粒小小赤霞珠入口,酸涩深刻宽广,清甜细微飘渺,一下子让人品出生活的味道。而藏梨有一种纯净的甜,干净,安宁,柔和,平缓,慢慢渗透心脾,心灵为之一空,便多了些宗教色彩。雨停风住。丝丝缕缕的阳光将树叶照得透亮,随处可见的白塔散发出明净的光芒,经幡飘动如蝶,一纸天空停在高处。援藏两个月的年轻同事脸上已经有了明显的“高原红”, 他正在放弃一个休闲城市养尊处优的生活习惯,努力接受偏僻、陌生和艰苦。而最不堪的是孤单,是深夜整座大楼只有他一个人的空与寂寞。他不停地说话,他说话时的欣喜像一道亮光在空气中摇曳。
庚子乡党委书记,一个干练的藏族女子,为她的政绩感到自豪,对未来充满信心。生活的意义其实并不神秘,幸福的密码往往就是生活的快乐和内心的安宁,有追求就有快乐,有皈依就有安宁。明天总是美好的。我对他们心怀敬意。人,人群,总是在进退之间,传承延续。祖先创造了辉煌的文明,曾经造就一个时代最好最风光的生活方式,他们以为那是理所当然的永远。然而自然灾害、战争、瘟疫在最短的时间以最简单的方式毁灭一切。又一代人只好后退,退回荒野,退回最初,茹毛饮血,繁衍后代,积累财富,养育文明,直到下一个轮回。
因为“一夫多妻制”,“金沙江河谷地带”曾经作为一种独特的人类学域名存在。很多专家在这里走访研究,探寻这种习俗的源流,也做出了多种解读。任何一种习俗,都取决于生存环境的安排,都是生存环境在人类心灵的折射,有的随着生存环境的改变而改变,有的融入人类血脉固执地传承下去。比如“一夫多妻制”,这种原始群婚制的遗存,契合了恶劣自然条件下家族繁衍、财富积累的需求,至今都没有被完全摈弃。女书记很认真地告诉我们,牧民集中居住,条件改善了,这种情况基本上不存在了。
午后,沿“金沙江第一湾”往北,走向得荣县城。金沙江就在眼前,泥浪滚涌,水声轰鸣,水雾蒸腾。江心往往有巨石,浪涌消失无踪,浪过突兀而出。江面狭窄,江水狠狠地冲击两岸,大浪轰然撞向两岸的岩石,撞成弧形的水幕垂落江面。“中国第一大河”上游的狂暴和急促此时展露无遗。这里真有那张图片上江青水碧的时候吗?突然想起“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的句子来,耳边就有了鸟鸣声声,但始终没有看见鸟飞过。
“得荣”也称“得隆”,意为“峡谷之地”,是康巴藏区的门户,西南与云南中甸、德钦接壤,北与四川巴塘和乡城紧紧相连,东北部与稻城毗邻。曾是巴塘土司的领地,民国时期属西康省管辖;解放初年成立人民政府,隶属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横断山系北段,群山耸峙,峡谷纵横,嘎金雪山海拔近五千米,其余诸峰多在四千米以上,山岭和峡谷落差高达两、三千米。得荣县就在这些山岭峡谷间,低纬度,高海拔,大落差,气候干燥,阳光充足,因而也被称为“扎西尼玛龙巴”,即“吉祥太阳谷”。
时近黄昏,县城街道依然拥挤。大大小小的车辆飞鸟归巢般涌向县城,长约四、五百米的县城主街道两边满满地停了两排,没有地方停放的还在往前缓慢移动。许多人穿行在车流之间。匆匆的,应该是机关单位的工作人员,下班了,急急忙忙回家。身着藏族服装,带着孩子的,应该是县城附近的居民,慢慢走过。行走更缓慢的,是穿着僧衣的人,看不出他们行走的方向。定曲河穿过县城,铁青色的水面涌动点点光斑,水声哗然。
主人极尽地主之谊。在热烈张扬充满宗教意味的祝酒歌里,衣香鬓影,觥筹交错。我们此行,当然有很多工作任务,我们都希望在那片还很陌生的土地上做出真正的业绩。主人的热情让人无法拒绝,大家很快入乡随俗。因为感冒,我头痛欲裂,很快仓皇退席,回房间和衣而卧。
我看见大片大片绿跌落在褐色土地上,一蓬蓬花开得姹紫嫣红;我看见一群人席地而坐,大地上响起宽广的梵唱;我看见一座座佛像庄严排列,檀香缭绕一笼笼烟雾;我看见无边的洪水倾泻而来,冰凉的感觉瞬间将我淹没……醒来时汗湿衣被,一种迟钝的酸疼深入肌骨。窗外已经有亮光轻盈地飘进来,定曲河哗哗水声一如昨晚。服了感冒药,换了睡衣,却再也无法入睡,只好起身出门。
清晨的天光飘洒在定曲河上,湍急的河水清亮新鲜,水声明朗轻快。青石垒成的河堤上,苔藓依旧葱绿,潮湿的味道在石头上蔓延。一个红衣僧人在河边人行道上慢慢走来,没有感觉出他的移动,他已经近在眼前。是很年轻的僧人,宽阔的额头,浓密的眉毛,黝黑的脸上有明亮的眼睛和干净的红晕。很快他飘过我身边,越去越远,不见了踪迹,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一群小孩突然跑过,一脸灿烂的笑转瞬即逝,笑声却在空气中久久飘荡。
太阳谷广场的标志性雕塑上,载歌载舞的姑娘和小伙子笑颜如花。我猜想他们应该代表了太阳和月亮吧,那是当地藏民内心崇高信仰的载体。广场上一片空阔,人群活动留下的风尘已经被晨风吹走,只有几个饮料瓶子心有不甘地留在角落。石碑上用藏汉两种文字刻着《太阳谷赋》,应该是这里的一种文化标志吧。因为对当地文化的陌生,而那些文字又在古奥与白话之间跌宕起伏,尽管全文诵读,却难解其意,只好抱憾离开。广场边沿坐着两个老人,一动不动,仿佛一直在那里,默默地看天空。我从他们身边走过,走到河堤附近,就看到定曲河的雪浪花一片片开放。回过头,老人已经消失了踪影。
作为对应的援建单位,我们有四十九名干部在得荣县开展为期两年的援建工作。他们在县政府、县级经济部门、一些乡镇担任副职,主要任务是找资金、建项目,加快当地经济发展。两年内,他们需要融入藏族群众,在尊重藏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的基础上,逐渐改善他们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增强藏区的发展能力。资金和科技并不难以送达,难的是民族心理的真正沟通与充分融合。尽管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诸多学科对此都有种种论述,也给出了多种方法,但是在实践中的成效却差强人意。
历史上,汉族统治区开发或援助少数民族区域的例子并不鲜见,比如秦汉之于南越、蜀之于彝区、唐之于吐蕃、两宋之于云南,直至清代的“改土归流”。这些开发和援助,有驻军屯田、移民开荒,有册封藩王、派官员管制,也有特殊的“和亲”“为一家”。但不论哪种方法,都以暴力作后盾、以少数民族“归化”为目标,为的是“千秋万世、一统山河”。从这个角度比较,如今的援藏显然是一种全新的工作,没有历史经验可借鉴,没有现成的方法去遵循,一切都需要智慧重新创造。
所以,尽管有诸多文件明确规定他们去干什么、怎么干,但是援藏干部一进入藏区遇到的最棘手的问题也许还是“干什么、怎么干”。他们需要放弃早已熟悉的生活方式,改变按部就班的工作习惯,努力寻找新的切入点,以藏族群众可以接受的方式开展援建工作。他们必须改变“投桃报李”的价值观,对援建工作倾注真情,以真正的热爱去接受面临的一切,然后奉献自己的力量。每个人都有梦想,我相信,他们绝大多数人是怀抱了梦想进入藏区的,他们憧憬着两年之后更加丰满的现实。
阳光明丽清澈,风慢慢滑动。沿定曲河北上。峡谷两边依旧一片葱绿,褪色的经幡在河上飘拂。万物安宁。一片叶子凋落,在阳光里撞击出金属的声音。车在一个老人身边停下来,同行的县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局长阿青和她大声说话。老人戴着帽子,稀疏的白发在帽子外面轻轻飘,一脸浅浅的笑,目光柔和安静。我想起那首《慈母》里母亲的形象——她正是阿青的母亲。我不知道她们用藏语交谈了些什么,但她们的笑容让我莫名地感动。那笑容,无比熟悉,又显得陌生,轻盈地进入心底,又仿佛本来就是从心底里飘出来的。
天空忽然很高,那一抹浅蓝深不见底。山峰峻拔高耸,灰白的岩石堆积成山体,岩石的锋刃历历可见。绿点点飘洒,仿佛随时都可以随风飞走。太阳就在眼前,多么清晰的太阳啊,须发毕现,纤毫分明,触手可及。忽然想起一个本土歌手的吟唱,“谁的遥望,给我一道光,照得我的飞翔天地宽广”, 一切以一种最纯粹、最质朴的方式呈现,所有心灵的震颤源于太阳,归于太阳。
峡谷里的平地上有一处牧民定居点。一片红顶白墙的房屋基本建成,房屋之间的水泥路面平整光滑。近处山梁上,有颓圮的土墙,看得出是废弃的房屋,不知什么时候、什么人居住过。走过那些房屋,更低的谷地里,卵石之间,一株不知名的阔叶草本植物鲜红的果实格外耀眼。密匝匝的果实挤成一团,形成孤单单的一串挂在宽阔的叶子下面。圆圆的果子形似我们在瓦卡看到的赤霞珠,却非常坚硬,表面上覆盖着一层蜡质,没有葡萄的柔软和水分。我想采下来带回城市,作为此行的纪念。同行的同事坚决阻止,于是作罢。慢慢走开。回头,一眼就看到那渐渐变小的红,心里突然一疼,然后为自己鲁莽的占有欲羞愧不已。
阿青决定另走一条路,让我们看看雪山风景。正是这个决定,让我们第一次体会泥泞地带行车的艰辛。看似平整的泥地,留下了那么多车辙,我们以为那一定是坦途。实际情况是,车一下子陷在了泥泞中间,进退无据。我们下车,在灌木丛生的路边和阿青聊天。阿青身体健壮,神情平和,目光明亮,一身藏族女装更让她显出干练和雍容。和我们说话的时候,总是望着远处,语调平静却给人以充分的想象力。
她的讲述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藏民的生育观念。因为对神的信仰,藏民对自己都赋予了神的担当。如果母子平安,那是神的恩赐。如果母殁子生,那是因为母亲的责任和价值就只是送子到人世,孩子出生,母亲即追随神祗离去。如果母子俱殁,那也是神的旨意。实际上,自丛林时代以来,人类对自身繁衍的渴求往往炽热、坦白而且无奈。生死皆神圣,所以要听从神的决定。从医学角度讲,恶劣的条件显然严重影响人的繁衍。但也正是恶劣的条件,赋予了这个民族坚韧、强悍、忠于信仰、敢于担当的天性,锻造了一种难得的人性美。
晚上,我们见到了四十九名援藏干部的大部分人。一名同事在最边远的曲雅贡乡工作,早上出发,到我们县城我们聚会的地方已经晚上八点。按照惯例,大伙儿拿出一个小水桶大小的茶缸,给他倒上满满一大茶缸子啤酒。他没有推辞,双手捧起酒狠狠喝了一大口,在大伙儿的欢呼声里傻傻地笑。大家什么都不说,端起酒杯一饮而尽,脸上的高原红和干干净净的笑,恰如晃动着的太阳光斑。
“金树枝啊,请绽开你那鲜艳的花朵;银树枝啊,别弹错你那动听的曲调;玉树枝啊,别掉落你那翠绿的叶子;远方来的客人啊,请别拒绝我的挽留……”耳边突然响起据说是为迎接文成公主的到来而演唱的“学羌”歌调,与定曲河的水声相应和。我知道那又是我酒后的幻听,是对大家兴高采烈的祝酒声的内心回应。但我却无法不希望这样的歌声在寂静的山谷里真的响起,希望太阳谷广场此时出现花枝招展的人群和曼妙的舞姿,希望一切被赋予生命和灵魂的事物此刻都翩翩起舞,将所有美好的梦想变成现实。
离开得荣的路上,我终于看到先后接纳了玛伊河和硕曲河的定曲河,在三道绝壁之间汇入金沙江。河流交汇处,清澈的河流像是被硬生生切断,代之以浊流激浪。那里的金沙江奔腾咆哮,显出吞吐一切的王者风范。送我们离开的两名工作人员说,你们遗憾啊,只顾工作去了,没有看到翁甲神山,那里珍藏着开启藏区一百零八处圣地门户金钥匙啊;没有看看玛伊河峡谷、莫木沟和下拥,那可是人间仙境啊;没有去香火鼎盛的龙绒寺,那真是有求必应的神灵啊……
我想,我的同事们一定会看到,那时,他们的梦想也许就实现了。
然而我什么时候能再次踏上这片山水?“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这样的句子此刻显得苍白。那位叫罗桑金玛的藏族歌手在高声唱:“我要回到,回到你身旁,陪你看太阳,看那高原的阳光,映红你脸庞……”
责任编辑 苍梧遥
上一篇:梁野情·中秋月(九首)
下一篇:在桥上书屋落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