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年悸动只为书
出于职业要求,常年要与文字打交道的缘故,因此常会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置身文字海洋的情景,觉得当时的每本书都凝聚了编辑的智慧和心血。书中的文章都很美,都是呕心沥血之作,是改革开放之初特定时期的各行各业、各色群体痛定思痛之后总结出来的花朵。每一本书都有着不同的吸附力,青年的我读得就特别投入,而像母校漳州师院阅览室里面的《台港文学选刊》这样特色鲜明的期刊,魔力超乎一般。
我是1985年9月到的漳州师范学院(去年改称闽南师范大学),就读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室在教学综合楼二楼中间,图书阅览室在同一层楼的末尾,是两间教室合成的,没人时很宽敞。全校就一个阅览室,来这里浏览图书的同学很多,尤其是夜间自习时间两个小时,通常都是人满为患,这时的阅览室就显得拥挤。我因近水楼台先得月之故,即使是白天的课间休息时间也去逛一下,就为了解解馋,过一下“书瘾”。当时最喜欢的就是《台港文学选刊》,但那时我并没有注意到它也是那一年才刚创刊,是期刊界的新秀。
在上漳州师范学院之前,我在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九峰镇念完初中和高中,家里穷,买不起书,所看的书都是同学之间传来传去的。镇里头有一个书摊,我只能从牙缝里省出三分钱去看一本小人书(连环画),五分钱看一本《少年文艺》、《雨花》等杂志,凭的都是个人兴趣,没有人指导。那段时间,还利用课余时间走马观花式看完《说唐》、《水浒》、《第二次握手》等有限的书籍,阅读面不宽,阅读能力其实很差。但是爱读书是真的,也爱写日记,初中到高中记了好几本日记,我上大学时,堂妹堂弟们偶然在我的旧书箱里翻到它们,争相阅读。
我就读的漳州师院总共办了三届的三年制教育,我去的时候是最后一届,这样,像我们三年制的85级学生与两年制的86级学生就一齐毕业,这就好像是86级学生增加了85级毕业生的工作分配压力!除此以外,85级的同学还经常被人戏谑说浪费了一年的工资。但我不后悔,反而心里喜滋滋的,觉得自己比学弟学妹们多了一年读书的机会。时至今日,我仍然在想,那时即使是四年制的专科教育我也能接受,才不管学历是不是本科,多读一年书,自觉就像是打铁多了一个关键的淬火时刻,可以打出更好的铁器。
我刚到师院时,一位学长给我开了一份书单,让我读完它们,说是给自己的专业垫底。书单虽然仅只是一张白纸,可是,这一张白纸黑字,让我觉得沉甸甸的。我拿着书单到了学校图书馆,比对之下,心中犯难,学长开的书都是大部头的世界名著、长篇小说,像《悲惨世界》、《红与黑》、《约翰克里斯多夫》等都在里头,每一本都有砖头重,勉强借出沉甸甸的两本,翻了几页后就放在枕头边了,还书时间一到赶紧归还图书馆。我觉得还是应该读自己吃得消而且喜欢吃的才好。
这样子,我进入学校阅览室的频率更高了。
在阅览室读书的情形有两种,一是从立式书架里抽取自己喜欢的新书,到旁边书桌那边坐下来看。另一种是坐在十米长的人字形固定阅读架前,阅读架斜角两边整齐排开各式各样的期刊,书本呈45度角摆放,用蝴蝶夹夹着,蝴蝶夹固定钉在木架子上。有的期刊杂志厚,像《十月》、《收获》是单本夹着;比较薄的就整个季度的几本夹在一起,《台港文学选刊》就是这样的。许多人是站着翻一翻这些期刊,而我不是,每一次进入阅览室就搬来一只塑料凳,首选的读书位置就是《台港文学选刊》,我自己都觉得那个位子好像是被我包定的一样。每次到阅览室,只要一发现《台港文学选刊》换上新一期的,心里就一阵悸动,如见到自己心仪的女子似的,假如有人坐在那里翻动它,我就在旁边坐下,急不可耐地等着他起身离开。
喜欢一本期刊而至于此的人,我相信一定为数不多。
相比较30年前其它书刊封面的简单朴素而言,《台港文学选刊》包装显得大胆而且前卫,用另一种说法就是精美、时尚。封面很多采用时尚女郎,或是台港影星,特别吸引眼球,一些没有接触过这本期刊的同学见我嗜好它,仅从封面判断,还以为我有什么不良心态。其实那时我着迷于诗歌,正是青春躁动热血沸腾的季节,整个中国仿佛都沉浸在诗歌的大潮中,不断有新的诗歌杂志和期刊诞生并涌向书架,满足广大青年的诗歌阅读需求。
但是,《台港文学选刊》选登的台湾诗歌却与我们大陆的诗歌不同,诗歌主题、选材与诗歌表现手法都不太一样,相比《诗刊》、《星星》大陆诗人的直抒胸臆、或沉痛反思的大主题,作品充满了对现实生活的否定与批判,台湾诗歌更注重意象、意境的营造,整体诗歌风格更生活、更感性、更乡愁、更古典,而且更多的反映生活的美好、情感的美丽,侧重巧妙表现生活的细节。那时候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只是冲着台湾诗歌更有浓郁乡愁气息与古典意境,我就迷上了它!我的一些作品发表以后,有一些眼尖的朋友会发现,作品的沉重感与我的年龄不相称,我想也是因为它。
读书的日子像九龙江水不知不觉地流走,而且匆匆,我在江水中浸润着,学校阅览室里头的《台港文学选刊》就像一盏航标灯,始终吸引着我这小小的渡河人。甚至,我觉得它既是航标灯,又是渡我的船,在我的阅读岁月中发挥着双重角色。
罗门、郑炯明、郑成义、岩上等一批台湾诗歌作者的名字镌刻在记忆的深处。罗门是这样表达《山》的,“那乳房/在天空透明的/胸罩里/裸着/它幽美的线条与形体/被海浪高谈阔论/它静静的/从不说什么”,在罗门的诗里,山变成了高贵的女性,让我这个从深山里跑出来的孩子浮想联翩;岩上是这样描写冲洗相片的《暗房》的,“昨天拍摄的照片/现在把它冲洗出来/不能有一点儿光线跑进/虽然只是那么一瞬/百分之一秒/虽然只是那么一点方寸/八分之一光圈/我们的爱/在心的暗房里/一张一张地重现”,习以为常的暗房居然可以与爱的题材扣得那么自然紧实,这也让加入学校社团、经常在暗房冲洗相片的我错愕不已,不得不佩服诗人对生活的强烈的感受能力!这几个诗人的作品,出现在1985年第三期《台港文学选刊》上面。
随后,纪弦、余光中、洛夫、羊令野等诗歌大腕纷纷涌入视野,他们的诗歌作品,像纪弦的《茫茫之歌》,余光中的《白玉苦瓜》、《隔水观音》等等都让我爱不释手、心醉不已,——《台港文学选刊》真真正正成为我的窗口,我从中看见台湾诗坛异彩纷呈的景象。
因为喜欢阅读,渐渐就喜欢上自己动手写作,鼓起勇气参加了校刊《丹霞》文学社、学校记者团,尝试着写了一些诗歌、小说、话剧等习作,教写作的老师就开始注意到了我。有一天,教我话剧的老师邱煜焜在课间休息时递给我一本证件,那是一本新书阅读评论员的证件,凭此证件,我可以自由出入学校的图书馆。比之同学手头都有的借书证而言,这本新书阅读评论员证件才真是对我的莫大的肯定和鼓励!
三年的师院读书生活转眼过去,我随着命运的风帆飘回到山里的一所学校。学校所在的山坡叫做赤尾岭,每次一阵狂风扫过,山坡上就会卷起漫天黄尘,云遮雾罩着山坡下的村庄。这个地名曾经代表着绝望,与我的青春一道,被湮没在岁月的泥泞中,——20多年前的一个大学毕业季,我与其他五个年轻人一起来到这所学校。学校后山有一条公路通往名字叫做白花洋的偏僻山村,从白花洋翻过几座山,可以到达隔壁县份永定县。当地人上山劳作时,从通往白花洋的小小公路往下望,嘴里面就会念叨着,“看,那学校多像是一只破漏的畚箕”。
在这样的一所学校里,刚从城市里回来的年轻人的心情可想而知,幸亏我的心中装着诗和书,在这段贫乏无聊身处孤岛一般的岁月里,阅读,成为我的最好的精神越狱。乡村虽然偏僻,邮政所还是有的,因此,订阅报刊是我迫不及待的安慰,而《台港文学选刊》就是订阅对象的首选。其他年轻人没有订阅图书的习惯,但是,每次到我的房间,看见书桌上的《台港文学选刊》,就顺手拿走借阅。我坚持阅读与写作的动力,很大一部分要归功《台港文学选刊》,是它让我感到阅读的快乐,是它让我隐隐约约看到“阅读改变命运”的希冀!尤其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独自坐在山区学校简陋宿舍里翻书,心里头总会想起在师院阅览室畅享读书的快乐的情景!
时至今日,从1985年至2015年,我与漳州师院、与《台港文学选刊》结缘正好30年,而这一份情缘,要感谢母校师院提供的平台!30年的时间跨度,我的工作岗位改变了,许多习惯爱好也改变了,但是原先对《台港文学选刊》的那一份美好感觉始终不变,在师院养成的阅读习惯依然不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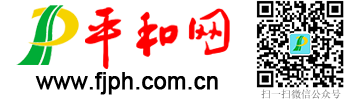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