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4版 :文化旅游

报刊搜索:
搜索
芒草花的开落



芒草,是故乡山头上的令旗,芒草一摇,秋风就冲过来了,天就冷了,芒草花就开了。芒草花一开,满山皆白,整面山坡看上去就像覆盖着一重轻絮。
故乡是个凹陷的土盆子,春天一到,芒草就成了盆沿上洗不尽的绿毛,疯长。芒草的生长随意性太强了,随便在路边一站就是一簇簇,一排排的,春雨甫降,它就在往年枯寂的芒草丛中挤露出新绿,柔软而舒展,到了盛夏,它就挺起修长的身子,很苗条,或者说是很瘦削才更确切些,但是因为它们总是密匝匝的群体出现在山上、田边、沟坎,总不会让人觉得可怜。在夏日明晃晃的阳光下,芒草会长出一串草籽,因为不可吃,所以人们不称其为果实。刚开始时,芒草叶片间吐出绿色的穗,朝天尖耸,此时芒草还是直立的。慢慢的,草籽逐渐胀大,穗串开始分叉,在暴雨与烈日的双重煎熬下,穗串越发长而饱满,枝串开始垂下,状如高粱穗,色泽渐变成红褐色,摸着像是少女新剪过的齐耳垂发,柔软而光滑。谁也数不清这一尺来长的芒草穗结了多少颗的籽儿!在草籽的重压下,芒草身子倾斜了,倾斜了的芒草更像极了一面令旗,在随时等待发出号令。
故乡人对芒草没有太多的热爱,也没有特别的怨憎。芒草虽然是草,可是却有着长长的茎,是有风骨的草,是草中的硬骨头,牛就不大喜欢它了。农妇有时把它收割回去,晒干烧火,可是晒干的芒草实在不耐烧,镰刀于是不太愿意光顾它。因此故乡的芒草实在是生长的很潇洒,很肆意,没有人对它实施计划生育,除非它一不小心长到人家的菜园子里头。近年来春节回乡,发现芒草长得更疯了,因为小时候的牛群消失了,镰刀隐没了,青壮年都到外面漂了,留守老人不能上山了,——没有牛蹄的践踏,没有镰刀的相逼,芒草甚至长到村子里废弃的老屋来了。
记忆中,芒草是有经济价值的,应该被颁于“经济作物”勋章的。四十年前的故乡,谁家不利用农闲上山割芒草?!我有幸在山上割了一星期的芒草,那是我上三年级的时候。某个上午课间操的时候,同班一个同学丢了一支圆珠笔。四十年前的圆珠笔可是稀罕物,整个学校都没几支,老师就很重视起来。有同学说,某某人第二节课下课时最后离开的教室。又有同学说,某某人第三节课时最早进入教室。很不幸,我无辜的名字在汇报者的口中反复出现。老师是个唇部有缺陷的青年,很严厉的开始了他的调查。在我们乡下有句顺口溜,一斑二矮三卷毛四豁嘴,说的是有这四种特征的人比较凶,老师是其中之一,当然是针对缺陷有采取补救措施的那种。自小接受农村文明熏染的我,对于这个老师的调查方式觉得无限恐怖,他手指头直戳我的额头:“把圆珠笔拿出来!要不明天全校开大会,批斗你,叫你跪在板凳上批斗!”
现在三年级小学生有谁会知道“批斗”是啥意思呢,可是四十年前,在农舍路边墙上涂满“斗资批修”、“铲除大毒草”等醒目标语、动不动就批斗“破坏分子”的年代,那俩字搁在任何一个成年人的心里都不啻是一颗重磅炸弹!我当时没有当场尿裤子就算是腿骨头够硬了,因为我行的端、坐得正。但我没办法解释,我当时就像一株无辜的芒草躲不开农妇的镰刀,我怕极了被拎起跪在板凳上批斗的情景,于是就没去上学。父母并不知情,他们每天早早就要出工,父辈们都要随着哨子声准时出现在田野里,他们就像会移动的草一样,每天栽在不同的地块里。祖母见我没上学,就叫我去放牛,又给我一把镰刀,交代说顺便割一捆芒草回来。未满十岁的我其时还不到割芒草的时候,割芒草卖钱是我的哥哥们的事情,是我父母亲的事情:芒草割回来放在屋顶上或者土埕边,几天后晒干,用心的轻轻的甩尽草籽,剥去枯叶,一摞一摞的绑好,剁齐根部,一捆一捆的扛到供销社去收购,——此前我一直没意识到那会是我做的事情。我没割过芒草,但是我看过呀,况且镰刀才多重呀,芒草才多重呀,我想我的祖母当时肯定是那么想的,于是我有了挥镰割芒草的经历。在山上,牛群散开觅食后,我对着高过我头的芒草挥起我的镰刀。平时在山上奔跑玩耍时,芒草经常割破我手我脸,稚嫩的皮肤会渗出连珠炮似的血珠子,伴随着还有微痒,锋芒毕露的芒草叶子,此刻悄声敛息,一排排躺倒在我的脚下。在芒草倒下的一刹那我似乎明白了,芒草虽高也怕我的镰刀!每割倒一株芒草,都会有几十、成百的草籽飞逸,像一团小小的烟雾腾起,像是芒草的灵魂飘散。我忘记了批斗,忘记了课堂,心里想的是收获的芒草卖了之后,哥哥或是父亲会奖励我几个纸包糖,或是几支铅笔。
我把割倒的芒草收拢成堆,又学着大人那样挑选茎秆粗大的,摞整齐了,两头捆好。芒草捆好了,却还未到回家的时候,于是就地躺下,以芒草为枕,仰望宁静的蓝天,这时候我发现身边的草都高过我,却并不打扰我,它们像我的朋友一样守护我,像电影里的解放军埋伏打敌人,草丛保护着解放军不被发现一样。那一瞬间我又感受到芒草的可爱,我真不该残忍的割倒它们,我是它们的一份子呀,你看,它们修长圆润的茎秆多像天使的手臂!空气中,刚才被我砍杀掉的芒草花仍像无数惊慌失措的虫子飘来荡去,四散飞扬,更远处,还有更多的芒草花不是因为我的缘故、而是因为风的缘故,也在四散飞扬。后来读书听到老师讲“草木皆兵”的故事时,我脑海里直接与芒草对上号。芒草花其实就是芒草籽,干燥的秋风抽干了它的水分,草籽不得不借助毛茸茸的末梢,借助风势逃离死亡的母体,去寻找新的落脚的土地,开启新的生命旅程。秋天的芒草花是画家笔下的白色颜料,把大山涂得花白,仿佛雪山一般,风一吹,雪花漫天飞舞,那气势真有如千军万马扬起的灰尘!秋天的芒草会再次变身,在风中甩掉所有草籽后,芒草重新直立起身子,没有了负担的芒须向天昂起,像一支支弱弱的草箭迎接严冷季节的到来。
割了一星期的芒草后的一个傍晚,父亲终于知道了我没去上学的事情,说要去学校找老师问清楚,可是话音刚落,老师就出现在我家门前的柿子树下,但不是原来要批斗我的那个。新老师瘦高个子,和气得很,一直关切问我为何没去上学,是不是病了,看来他完全不知道有人要批斗我。木讷的我支支吾吾的说不出话来,老师就说明天要准时去学校上学,再没提起批斗的事情。原来那位唇部有采取过措施的老师是临时代课的,正式的老师来了,他就走了。成年后我每每想起童年时的这一场虚惊,我始终没有去落实那位老师是否真的要批斗我,也许他只是随口胡诌吓我,是他那种水平的人所只能够采取的简单而粗暴的处事方式,并非真的要批斗,只是没想到我这么胆小,竟然吓着了,他那句关于批斗的语言像是最锋利的芒草叶子,割破了我的童稚岁月。那时老师许多是大城市里的教授,或是上山下乡的知青,人事调动频繁,小学的老师就像芒草一样换了一茬又一茬,我最记得他俩,一个吓我,一个救我,一个是临时的,一个是正式的。时至今日,网络上一披露什么“暴力执法”事件被曝光,相关责任部门就推卸给“临时工”时,我觉得我应该是最能够理解这种现象的,因为我也曾经像芒草一样被精神暴力过。
岁月悠悠,芒草花开又落,落到地上的草籽儿谁也看不见,可是它却用这世界上最为轻柔的草籽微粒去占领故乡肥沃的土地,一根茎撑起数百成千的籽,飘散后所占的土地何止几亩!我不知道,我的乡亲是否受芒草的驱使才离开自己的土地、远飘到东西南北的城市里,我不知道他们能否在城市里扎根,或者是到了后来,他们终将变成芒草被城市所铲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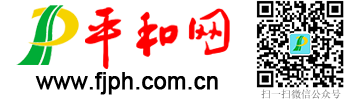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