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

平和多山,上千米的山峰就有31座。最有名的是灵通山,火山地质公园,贵为漳州唯一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因为有南方的悬空寺灵通岩而成名已久,黄道周也曾登临留墨。最高的是闽南第一高峰大芹山,如今茶香满山,不久也将樱花满园。这两座山的风景不在山顶,灵通山则是悬崖峭壁,不易攀登,我心有所想,却都没能爬上山顶。我真正登顶的是平和的第二高峰,平和与永定的界山仙洞山,海拔也超过1500米了。山顶上有座石垒的小庙,香火很旺,但属于永定。平和还有一座待开发的太极峰,山本身平常,是山上星罗棋布的奇石让它身价倍增。去看那些造型各异,各有奇趣的石头,没有标准意义上的路,尤其是到“闽南之根”巨石的后半程,要手脚并用,溜走并举才行。我去过三趟,最后一趟是早上7点从城里出发,晚上7点才回到城里。到开始步行的半山,单趟车程不用一个小时,其他的时间一半多在路上。行行摄摄,也乐在其中。
这些山,林语堂都没去过。他爱山,看山,也常常登山。但那都只是坂仔的山。他十岁离开出生地坂仔乡,如今的坂仔镇,坐船沿着花山溪到漳州,再到厦门求学,之后只是在假期回家省亲度假,他的故乡登山运动只能在坂仔周边。坂仔那些山都很普通,除了十尖山巍峨挺拔,其他的山在福建,在平和都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但这并影响林语堂对故乡青山的热爱和思念。就像人们不会因为母亲的美不美而减少几分对母亲的依恋。“如果我有一些健全的观念和简朴的思想,那完全得之于闽南坂仔之秀美的山陵”。坂仔的青山已经深入到林语堂的血液之中,造就了他的高地人生观。
故乡的群山曾带给童年的林语堂无尽的遐想。坂仔花山溪畔的林语堂故居,遥对着坂仔的最高峰十尖山。林语堂出生房间里,有一扇向北的小窗,林语堂小时候常常爬出窗户,骑在比窗户略矮一些的屋脊之上。在那里,可以远眺十尖山,也可以近看花溪水。他说:“我常常站着遥望那些山坡灰蓝色的变幻,及白云在山顶上奇怪的,任意的漫游,感到迷惑和惊奇。它使人轻忽矮山及一切人为的、虚假的、渺小的东西。这些高山早就成为我及我信仰的一部分,因为它们使我富足,心里产生力量与独立感,没有人可以从我身上带走它们。”在自传体小说《赖柏英》中,林语堂更是借主角之口说明了这些山对他的世界观起着怎样的作用:“你若生在山里,山就会改变你的看法,山就好像进入你的血液一样……山的力量巨大得不可抵抗。”
年少的时候,山,就是一个巨大的诱惑。我也是山里长大的孩子,那儿的山要比林语堂家乡的山来得更近村庄。少年时期,也很喜欢看山。看山岚在远山里飞舞,看白云在天空里演戏,看着看着就发呆了,想山那边有什么?奶奶说:层层山后有人家。日暮的时候,我又想,他们什么样?在干什么?长大了,去过的地方多了,我知道,山外青山楼外楼,太阳底下没新鲜事,山那边的人和我们一样,一个鼻子,两个眼。但只要看不到,我还是会想,视线的尽头,在哪里?山那边,有什么?日出的时候,想到东边的山峰看日出;日落的时候,想到西边的山峰看日落。每天的日出日落都不一样。上世纪七十年代不能在农田里建房子,能建房子的土地非常稀缺,父亲只好在半山腰里建了一栋房子。那房子的位置比原来的村子高有一百多米吧,很适合于远眺。暑假的时候,我有时一个星期都不下山,常常坐在屋前,看书,看山,听风,听雨。看鸟,将天空越飞越高。看云,把天空还给了眼睛。
对于山里的人而言,山不是用来看的。山,是山里人讨吃的地方。林语堂是牧师的孩子,不用干山里孩子的活,比如到山里砍材,搂草,摘蘑菇,收地瓜等等。干这些活,要走很多山路,很辛苦。我去外婆家,要走三四十里地的山路,去奶奶的娘家,也要走15里地的山路,都要翻过一座上千米的大山。那时,真恨山太高,路太陡。林语堂的祖籍地在漳州近郊的天宝五里沙,那时从平和到天宝,走的是水路,山,只是两旁的风景。
但山也是山里孩子的启蒙课堂,游戏天堂。四月,正是红杜鹃盛开的季节,记得小时候,常常清早就到附近的山上采杜鹃花,把花蕊拔掉,鲜嫩的红叶有淡淡的甜味和花香。一年假期,朋友一早就带我去近山采松针,上面包裹有蜂蜜的松针。将松针放进嘴里舔,很甜,伴着松针的清香,很是美味。这些,都是现在城里的孩子不可能有的最生态的记忆和美食。我想,调皮的林语堂小时候也会干这些事吧。
长大以后,假期回家,采蜜的事干得少了,更多是没有目的登山。绕着老家后面的山脊走,是最经常的事。有一年正月初一,还带着两个妹妹从老房子的后山出发,沿着山脊,走了三四座山脊,就从采过松针的山谷下山回家。有一年春假,正月初三吧,村子被大雾弥漫,突然就想登高看看雾海,于是就带着外甥们开车直上白云岭。待我们在七弯八拐的盘山公路上穿出迷雾,站在到另几个高山村的山口,只见自己所在的大村子和附近所在的地方,以及那些较矮一些的群山都被大雾淹没。放眼望去,雾海茫茫,远山如岛。雾海不像云海那样波涛汹涌,起伏不平,有一种平和、宁静的壮美。
登高的诱惑,是巨大的。看山不如登山,仰望不如俯瞰,这是诱惑之下的必然。《圣经》说:“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山里长大的孩子,那脚天然善于登山。山压服一切,大山使你谦卑。但登高的诱惑,眺望更远的远山的诱惑,让我们忘却了登山的艰辛。山高人为峰之后,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群山汹涌成波涛。主席在橘子洲头,指点江山。山里的孩子,在山巅想望山外。
站在山上,尤其是在山顶上,看山下的村庄和人们,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虽说还没有达到神的高度,却也已经和凡尘有了一段距离。距离产生美,高度拓展视野。平时感觉杂乱的村庄因为远了,有一种自然的美感。在高山面前,在山的脚下,也就是自己的脚下,人,多么渺小。辛辛苦苦的人们,如蚂蚁一样来来往往。一种看戏的感觉,一种悲悯的情怀,一种四顾苍茫的孤独,油然而生。说芸芸众生的时候,潜意识里你的位置就在高处。这,也许就是林语堂所说的高地人生观吧。如今的城里,高楼林立,人很孤独,也很卑微,很飘忽。只有山,才能给人以安全感、责任感和向上的引领。
长大以后,登过很多名山大川,庐山的云雾,黄山的烟雨,华山的险峻,泰山的一路文化大餐,新疆天池的西天传说,长白山天池的冰天雪地鸟飞绝,这些都用脚丈量过。但那些山,更像大美人,少了一些亲切。就像林语堂念念不忘的是坂仔的山一样,故乡的山才是亲切的,如亲人,可亲,可近,可资经常性的思念和回忆。
名山,更多是美学上的回忆,文学上的记述。如明月之于文人,夜之于美女。
不知道林语堂有没有月下登山的经历?他的文章中倒是常说起江上清风和山间明月,为此还被一些人批评说有小资产阶级的情调。对此林语堂感到好笑,说那些批评他的人都是自幼即居于都市,他们又怎么能知道一个农家子的感受呢?“在他们看来,好像清风明月乃是资本家有闲阶级的专利品。”不能不说的是,登山不小资,赏月也不是文人的专利,但爱山间明月,领略月下的群峰的幽美,却不是普通的山里的孩子所能领略的,那真的是文人的情怀。“赏风景,月下最好。清风徐徐,不知此处是何地。看美女,灯下最妙,烛光尤佳。烛影摇红,谁知今昔是何年。”十多年前的一个周末,我去一个文友的葫芦山寨后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已经不是懵懂的山里少年,也算是一介文人了。
女作家林百说:“我迷恋月光下的事物由来已久……”。这文字就有些夜的魅。女人,多有猫性。尤其是女作家,猫性更甚。而猫,从来都是夜行的动物,有一种夜的神秘和妖冶,注定在暗夜中思春,却可以享受无边的月色。林语堂是儒雅的学者与文人,这两类人都有女性的细腻和敏感,能够享受夜,享受月,享受月下山峰的幽美。
曾经坐车夜行在峡谷和群山之巅,一轮圆月辉映下的山峦、树木有柔美的、流动的莹光。也曾坐车在月下穿过戈壁,窗外无数朵白云就像酣睡的绵羊触手可及,真实而又梦幻。但我第一次在群山之巅领略到月色的动人,是在武夷山的天游峰。十九岁的那年秋天,和两个同学结伴到武夷山穷游,农历九月十五的晚上就住在天游峰顶。白天爬了几座山,累得我们吃完晚饭就躺下睡了。夜里九点多,我们不约而同的被床前明亮的月色所惊醒。睡意全无的我们赶紧起床跑到了大殿——宋美龄在那举办过舞会----前面的草坪。那个晚上,整个天游峰就我们三个游客,服务员也到山下看电影去了,四周非常的安静。天游峰地势较高,放眼望去,只有东侧的大王峰和南面的狮子峰高出群山一头,警惕的守卫着这已经安睡的碧水丹崖。在山脚下拐了一个大弯的九曲溪犹如卷曲着身子熟睡的少女。山谷里飘着淡淡的山岚,就像披在少女身上的轻纱。山下传来的人声感觉很遥远,很遥远,没有一点烟火味。月圆,天高,野阔。我们坐在石栏杆上,就像坐在天庭那南天门的台阶上。如水的月色静静地倾泻在白色的栏杆上,荡漾在凝固的波峰里,发出悦耳动听的声音,闪耀着天界的静谧。
峨嵋金顶的月色却是另一种况味。坐在海拔三千出头的金顶的石头上,上山时穿着夹克衬衣的我们此时不分男女个个裹着草绿色的军大衣。西北的雪山在月光下闪着幽幽的蓝光,南面的空谷却雾气弥漫。身旁的石地上,一洼一洼月色透着寒气。凛冽的月色,散发着千年的神秘,万里的苍凉。连炉火正旺的我们也无法消受,只好躲进气象局招待所的铁皮屋缩进被窝,让如水的月色在屋外独自漂泊。如我们的祖先,想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却无法听见。
体会到月色的神奇,却是在四川大淝水的原始森林。由于是刚开发的景区,又是五一,游客很多接待能力却非常有限。我们到达第二个简易的住宿点时,仍然没找到住的地方。六个人,吃的也只是一盆清水里放着几片菜叶,两块肥肉,饭倒是管饱。我们只好沿着小溪来到一个凉亭里,点起篝火,下棋聊天。到了午夜,山谷风生,月凉如水,坐不住的我们便趁着月色上山。穿出一片高山杜鹃林后-----高山杜鹃的花朵很大,月下更是妖媚,我们走进了斜斜上升的一个乱石谷。乱石有的大如桌面,有的小如小鼓。大大小小的乱石在朦朦胧胧的月色下,表面都氤氤着一层岚气,好像是一群有生命的精灵,在蛰伏了一天之后出来在此聚会聊天。走到山谷中程,突然出现一棵没几根枝条的枯树,那感觉也不是长在人间的树,而像是披着仙衣的一个老者。或者就是在看守这些精灵?很快,我们就不真实地走完了这不长的乱石谷。乱石谷妖冶的奇美却让我第二天下山时一直在寻找这段山谷,但一直走到山下也没发现这山谷。坐在车上,我才想起刚才是走过了一段乱石谷。在白天,没有了月色的魔力,石头又被打回了原形,枯树只不过是一棵毫不起眼的枯树。太大的反差了。是月色,让一段毫不起眼的乱石山谷成了仙境,让我二十多年后还没忘记。
林语堂如今也是一座山峰,文化的高峰,文学的高峰,也许不是中国最高的,但也和他故乡的十尖山一样巍峨挺拔。好在这十尖高峰是平易近人的,可亲,可爱,可常常登临的。“十尖石起时入梦,为学养性全在兹。”这是坂仔之幸,平和之幸,我等众生之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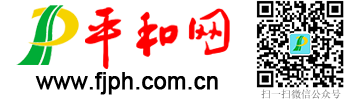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