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茶香比那春天更悠长

骑着摩托车拐出小区汇入街上车流人流的时候,有几粒雨点滑落春天的夜幕,击打在我的脸上,疲惫的脸颊顿觉清爽起来。这是春天,凉风习习、空气中没有一点浊尘。街上的风景树把城市的灯光隔成一道道的栅栏,一道明一道暗,让我仿佛回到故乡牧牛的林荫山道,回到童年赶赴学堂种满油桐树的公路上。很快来到邀约聚集的场所、闹中取静的茶楼,受到茶楼外广告牌上巨大“茶”字的触动,我的鼻翼条件反射地吸动几下,仿佛浓郁的茶香从茶楼四周喷涌而出,顷刻把我笼罩。
饮茶成为时尚,成为酒局和饭局的美妙序曲和升华,这是自小穿梭在茶园里的我所始料不及的。
印象中,父亲是村子里种茶的领路人,种的是“梅尖”、“毛蟹”。春季,雨水充足的滋润之后,梅尖的叶梢窜的老高,有近一尺长,一小撮一小撮的簇拥在茶树上,在风中轻舞着傲人的身姿,但是这种茶采摘容易加工难,加工之后茶叶片卷曲,看上去仅剩下老长老长的茶梗,必须用剪刀剪短了才好卖。毛蟹就不同了,它长不盈寸、成片卧伏的样子,採茶时略嫌难采,但是容易加工,而且,它的味道比起梅尖好一些,加工得好的话有兰花香。那时候,大队有茶山,小队有茶山,父亲也有,但不是茶山,只能叫茶园,一小片而已。“十岁上大人样”,山里的小孩过了十岁的生日,无论高矮,都得上山或下地,干不了主力打打下手也行。因此,大队或小队採茶时,大人们老老实实站在茶树前一株一株依序采过去,小孩子则背着与身高差不了多少的茶篓在茶山上乱跑,哪儿的茶叶长势好、嫩芽窜的高就奔向哪儿,不像大人那样好好地采而是俩手乱抓。采不到半茶篓,背在身上嫌重,就提到统一收茶的会计那儿称好倒进大竹筐里。小队老会计是个被称作“秀才”的人,衣服左胸部插着笔,有时一插俩根,不像其他人什么也没有。老会计在本子上记下各家小孩子採茶的斤两,回到队部再折算成工分。小孩子其实采不了多少茶,不到小半天就闹採茶的手指痛,就跑到就近茶园外的山上寻找野果子去了。
在家乡,茶与辛苦是同义词,尤其是暑天,野外烈日下採茶,室内高温中翻炒,夜以继日的烘焙,手、脚因茶汁的浸染而乌黑,头发因粘满茶叶茸毛而花白,双眼则因熬夜而通红。制茶之时,茶香飘出低矮的农舍,可以溢满全村,可以让外边的人驻足感受,而屋内的制茶人对于那浓烈的茶香却了无知觉。父叔辈们制茶时腰间都要绑着一条汗巾,擦过汗水,一绞汗巾,汗如雨下,滴答作响。大队小队集体制茶时几十个大人在一起,大家嘻嘻哈哈的有说有笑,互相说些消遣的话,熬夜制茶的辛苦感觉弱了许多。倒是各家各户的茶开采后,自家几个人闷头制茶的情形,真是让人觉得累得慌。十天半月之后,茶叶採完了,加工好了,祖辈父辈们各自大睡一觉,然后带着未尽的疲惫登门互访,互相品尝,互道茶情。有因时间、火候把握得好、茶香醉人而沾沾自喜的,有因时间火候没把握好、茶味糟如猪食而骂骂咧咧的。茶叶烘焙的温度还没冷却,只隔座山的广东大埔的茶贩子就来了,劣茶一拱手就到他们的巨大的布袋中,不用怎么讲价。好茶也多搁不了三、五天,老实的茶农们挡不住茶贩子们关于市场行情颠三倒四的吓唬。当乡人手中攥着簿簿几张钞票时,他们又经常懊悔起来,怎么就不多坚持一阵子呢,再放它几天说不定就能卖出更好的价钱呢!浑身臭汗尚未散去,茶叶却“轻舟已过万重山”了,好茶被茶贩搜刮一空,留下的往往是一些出不了手的劣茶自用。茶香到底怎样,他们懵然失忆。
出生山里,可谓在茶的苦水中泡大,我满心里装载着家乡人为茶辛苦为茶忙的劳碌形象,也因此我的人生旅程总有茶相伴。小时候,家里有客人来,父亲就会先起好小火炉,放上水,拿张小凳子叫我坐在旁边,用小竹扇把炉火扇地旺旺的,大人们却坐在临时当做茶几的饭桌边抽烟聊天等水开泡茶。要是等急了,大人们就会开起我们“小孩子屁股三斗火”的玩笑了。等茶泡好,客人会说“你刚才烧开水那么认真,也喝杯茶”,我就端起一杯喝,苦苦的不好喝,就跑开了。我很不喜欢给大人扇炉火,大人泡茶时谈话比其它场合显得正经,似乎有一种小孩子经受不起的压力。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泡茶,是我14岁那年夏天的一个夜晚,父亲带我走路到三公里外邻村大伯父家里。大伯父是个威严的人,坐在正厅八仙桌旁左边的太师椅上,父亲坐在另一边,我则有些紧张地把自己端放在八仙桌前的一把长条凳上。煤油灯照着他们兄弟的脸,他俩的脸上写着某种商量好的秘密。30多年过去,那晚的夜色和两个大人的脸色合成某种神秘的力量,一直流淌在我的血液里。大伯母一会儿就端上茶来了,大伯父就叫我喝茶,茶是什么滋味已经全然不记得,只记得我一边喝茶一边回答大伯父的询问,语文、数学、英语各多少分数,那是中学初一年期末成绩。依稀记得大伯父对我的成绩还算满意。之后不久,新学期开学了,我告别了乡村学校、被父亲送到相隔近20公里的古镇上学,这个结果是那个泡茶的夏夜商定的。在古镇上学时候,我与茶结下不解之缘,但是喝茶不叫“饮”,不叫“品”,叫“灌”。在租住的老房子里,用红泥小火炉煮好一陶钵水,没有茶壶茶杯只有大约可装一斤水的搪瓷牙缸,取一小撮茶叶放进去,泡上开水,稍等凉些,咕噜灌下,喉间没有留下什么味道,摸摸肚子,却有浑圆充实的感觉。如此之举,不是贪婪茶香,只是为了赶走磕睡。彼时彼地的我,磕睡不起呀。19岁上,家乡茶陪我登上了九龙江畔的高楼,我的青春从此插入一段难忘的滔滔水响,更不能忘记的是铁架床上、放在枕边的布袋茶,那是制茶打包专用的粗布袋,因为浸染茶汁,白布变成褐色,包着茶时圆如地球仪,打开有一米多长,每次喝茶拿茶叶打开布袋,就像打开一个旋转的地球。以粗茶为伴,我每天都在茶香氤氲中告别黑夜,又在茶香氤氲中迎来黎明。父亲每次托人寄茶来时都会说,那是好茶。九龙江边,楼高风大,吹去了春夏,吹去了秋冬,可是茶香却怎么也挥之不去,悠悠,长长。彼时彼地,每当我深夜翻书看到有关农人劳作的描写,我脑海中总会浮现父亲制茶的情景,因为低头使劲打包踩茶,豆大的汗珠从额心流向鼻尖,越聚越大,最后砸落地面!
春去春又来,我的人生轨迹始终没有离开过茶乡。家乡好多茶园跟不上现代农业的步伐而荒废了,野草丛生。单打独斗各自为阵的经营方式,不可能给村人带来什么可观的收入,许多青壮年只得挤上开往广东各地的汽车,去城里头做面包,做沙发,一带俩,俩带仨,仨带一大帮,渐渐地村子里仅剩下九九三八六一番号的留守部队(九九指代老人,三八指代妇女,六一指代儿童)。我回乡再也看不到村姑满山遍野採茶、与年轻人呼来唤去的热闹场景,闻不到制茶时弥漫全村的苦味茶香,就更别说那深烙心中的红色小陶炉和那被粗糙的手扇得呼呼叫响的木炭火苗,——却有越来越多,更加优质的茶叶上市,城市里茶楼林立,偶尔经过某个街区闻到茶香馥郁,我总会驻足寻找,那里肯定是一处加工茶庄。
又是一个朋友聚会品茶侃大山的夜晚,茶几上,小姐细腻的手在茶杯、茶壶、茶炉间穿梭巡回。看着滋滋作响的电磁炉,我心却在怀念着以前的红泥小火炉:彼时的粗陋与慢拍,如今的精致与快捷,彼时的岁月,如今的茶香,人生的时空须臾错乱,人与岁月,了然遗忘,分不清是遗失还是收获,在恍惚的精神世界里。而现实是我骑着摩托车,呼啸着离开了童年,远离了山野,进出在现代化却力求仿古的茶楼,在春风荡漾的夜里品尝新上市的春茶,茶水冲泡之间,雾汽袅娜蒸腾,茶汤金黄,茶香芬芳,绵绵长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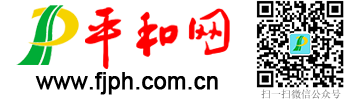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