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语堂与陈锦端

“我不免想到,在父亲心灵最深之处,没有人能碰到的地方,锦端永远占一个地位。”(《林语堂传》林太乙著)这是林语堂的次女林太乙笔下的描述,诚如林太乙所言,在林语堂的心目中,陈锦端永远占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位置,这地方柔软、隐蔽,却完全是真情浸润。林语堂和廖翠凤的婚姻佳话广为流传,但对于林语堂来说,廖翠凤是生活伴侣,但他最为挚爱的却是陈锦端,陈锦端是他的精神高度。
林语堂和陈锦端相识在上海,当时正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的林语堂和陈锦端的哥哥陈曦庆、陈希佐是同学,而陈锦端当时在与圣约翰大学一墙之隔的圣玛丽女子学校学美术。与陈氏兄弟往来密切的林语堂自然也就有机会和陈锦端见面,第一次见面,他就为之倾倒:“她生得确是其美无比”(《八十自叙》90页),一见钟情让一向机灵善辩的林语堂也显得木讷起来。在林语堂的眼中,陈锦端天真浪漫,而且洋溢着青春的气息,还画得一手好画,所谓的“情人眼里出西施”,林语堂把陈锦端当做美的化身,认定她就是自己追求的人生伴侣。这不仅仅是林语堂的“剃头挑子一头热”, 林语堂“接连四次走到台上去领三种个人所得奖章,以及以演讲队队长身份接受演讲比赛获胜的奖杯”(《八十自叙》90页)在圣约翰大学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博学多才的名声也传到圣玛丽女校,他的“英俊有名声”也俘获了少女陈锦端的芳心。两情相悦让他们越走越近,以致林语堂在教堂做礼拜功课的时候也心不在焉,陈氏兄弟自然看出其中奥妙,所以当陈锦端和林语堂在一起时,他们总是知趣地与这对恋人保持适当的距离,避免影响了气氛。
坠入爱河的林语堂和陈锦端自然无法免俗卿卿我我的陶醉,陈氏兄弟的有心成全让他们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多。有一回,他们倚靠在一棵相思树旁,四目相对。无法表达自己快乐的林语堂,大谈特谈他对“艺术”的见解。他谈起孩提时就立下的志向:“我要写一本书,让全世界都知道我林语堂!”陈锦端也脱口而出马上回应:“我要作画,把人世间的真善美化作无声的语言,用我的画笔,把它们全部融进我的作品。”“人是肉和灵互相混合而成的。人活在世界上,要睁开眼睛看天地之奇妙、宇宙之美。当然,我更要欣赏挚爱的女孩。”(《林语堂传》林太乙著)面对陈锦端“你理想的女人是什么样子的?”的发问,林语堂神采飞扬:“我心中理想的女人是芸娘,她能与沈复促膝畅谈书画;我最崇拜的女子是李香君,崇拜她的憨性,爱她的爱美,当然,我最爱的女孩就是眼前的你……”(《林语堂传》林太乙著)这样的甜蜜无法言说,陈锦端和林语堂陶醉的不仅仅是话语,真情是他们共同的发酵剂,把日子过得每天都是风景。
但好景不长,放假的时候,林语堂以寻找陈氏兄弟为由,经常出入陈锦端家,一向开朗大方的陈锦端却害羞地躲进房间。陈锦端的父亲陈天恩,这个厦门的富豪、名医很快就发现了其中的秘密。他当时想到的是为陈锦端寻找一个“金龟婿”,显然林语堂这个穷牧师的儿子,这个对基督教不坚定的圣约翰大学学生不在他的选择之列,尽管林语堂很聪明。陈天恩迅速出招干预,他告诉林语堂:他以为陈锦端定了亲。这个消息对林语堂而言肯定是个晴天霹雳。他回到故乡平和坂仔,神情忧苦的他努力疗治内心的创伤,善良细心的母亲发现不对劲,于是在晚上提着灯笼到了林语堂的房间,询问详情。强忍伤痛的林语堂再也忍不住,放声大哭,哭得瘫软下来。母亲的安慰也许无法完全解决林语堂的痛,大姐瑞珠的责骂“你怎么这么笨,偏偏爱上陈天恩的女儿,你打算怎么养她!陈天恩是厦门巨富,你难道想吃天鹅肉?!”这阵骂把林语堂骂清醒了,林语堂慢慢从被陈天恩拆散他和陈锦端的阴影中走出来,但他并没有忘却陈锦端的身影,而是把她在自己内心深处藏了起来。林语堂为家乡坂仔的初恋女友赖柏英撰写了自传体长篇小说,对夫人廖翠凤更是着墨不少,而陈锦端却很少提及,到晚年,他在回忆录《八十自叙》中对60多年前的这场热恋也是语焉不详,仅仅在第五章“我的婚姻”中略有涉及,而且隐去了她的真实姓名,仅以“C君”代替,称其为“其美无比的大美人”。这份情感于林语堂是隐讳,他把这份情感供起来,藏得很深,却从不曾遗忘,即使岁月风雨,即使他后来漂泊各地,但陈锦端,依然以当年的青春、天真和多才多艺的美好形象存活于心灵深处。多年之后,曾对爱情痛彻心肺的林语堂在小说《红牡丹》之中借红牡丹的口道出对爱情的理解:“真正的爱情是一个不可见的鸟所唱出来的稀奇的无形无迹飘动而来的歌声,但一旦碰到泥土,便立刻死去。情人一旦成了眷属,那歌声便会消失,变了颜色,变了调子。唯一能保持爱情色彩与美丽的方法,便是死亡与别离,就是何以爱情永远是悲惨的缘故了。”这样的感受颇有杜鹃滴血的悲情。
陈天恩也不是简单地拆散林语堂和陈锦端,他把隔壁钱庄老板廖悦发的女儿廖翠凤介绍给林语堂,林语堂知道自己和陈锦端无法成为眷属之后便接受了廖翠凤,四年之后他们结婚了。他们的爱情由结婚才开始,是以婚姻为基础而发展的。失去林语堂的陈锦端也痛苦万分,她拒绝了父亲安排的金龟婿,只身远赴美国米希根州的霍柏大学攻读西洋美术,学成归国后在教会办的上海中西女塾教美术课,全身心投入到教务中。她一次又一次把他人拒之门外,一直单身独居。直至32岁时,才与厦门大学教授方锡畴结婚,长住风光如画的厦门岛。她终生未育,抱养了一男一女。
林语堂的心中一直眷念着陈锦端。当年林语堂从国外留学回来之后,辗转多地然后定居上海,同住上海的陈锦端经常去看他,每每到陈锦端要去看他的时候,林语堂都当成大事,林太乙就曾经描述“父亲对陈锦端的爱情始终没有熄灭。我们在上海住的时候,有时锦端姨来我们家里玩。她要来,好像是一件大事,我虽然只有四五岁,也有这个印象。”廖翠凤也经常拿这件事来开林语堂的玩笑,“父母亲因为感情很好,而母亲充满自信,所以会不厌其详地、得意地告诉我们,父亲是爱过锦端姨的,但是嫁给他的,不是当时看不起他的陈天恩的女儿,而是说了那句历史性的话‘没有钱没要紧’的廖翠凤。母亲说着就哈哈大笑,父亲则不自在地微笑,脸色有点涨红。”(《林语堂传》林太乙著)潇洒、闲适的林语堂一碰到陈锦端这个软肋,那种不自然显得尤为可爱,也是触碰到他内心禁区的在乎。他对陈锦端念念不忘,到了老年的时候,他在笔耕之余也作画自娱自乐,他画的女孩总是一个模样:留着长发,再用一个宽长的夹子夹在背后。固定的发型让女儿不解,面对女儿的发问,林语堂并不隐瞒他创作的原型,抚摸着画纸上的人像,直接了当地告诉女儿:锦端的头发是这样梳的!简单的一句话,流露出多少历经岁月汰洗之后的浓郁真情和那份难成眷属的痛。直到耄耋之年,病魔缠身,靠着轮椅活动,还念念不忘半个多世纪前的那段旧情。1975年,林语堂住在香港三女儿林相如家。一天,陈锦端的嫂子、陈希庆的太太登门相访,寒暄之后,林语堂问起音讯不通多年的恋人的情况,当听说陈锦端还住在厦门时,他那有些浑浊的老眼忽地一亮,双手硬撑着轮椅的扶手想站起来,并高兴地一连声说:“你告诉她,我要去看她!”(《林语堂传》林太乙著)
一向通情达理的廖翠凤知道和理解丈夫对陈锦端的那份深情,但此时她也忍不住说:“语堂!不要发疯,你不会走路,怎么还想去厦门?”林语堂听罢,颓然躺倒在轮椅上,喟然长叹。这声长叹不知道是否是60年前那份痛的延续,但那种无奈想必又弥漫在这个老人身边,或者说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老人,只是从内心深处流露出来,成为那份岁月的感慨。几个月后,林语堂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多彩多姿的世界和他所挚爱的人,离开了陈锦端,离开了人世。几年后,陈锦端也辞世而去。他们的相继离世给跨越了数十年的恋情悄然画上一个句话,成为一个传说,在别人的记忆和文章的字里行间流传。只是那份痛,只有他们两个人都能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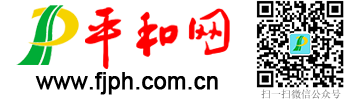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