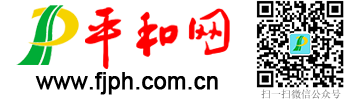如是你爱,请你放开
编辑按:
阿杜在天桥下唱着《撕夜》的时候,我在七道堰街上成日听远叽哩咕噜地念叨Jay的《半岛铁盒》。
长头发的男人总有一种美,比如年轻时的齐秦,比如《东京爱情故事》里的三上。CD盒封面上的阿杜略侧着脸,几绺发丝随风拂漾着脸庞,似隐含着一丝笑意,眸子里却透着一丝忧伤。
我发了疯地喜欢上他那沙哑的嗓音:ANDY,活着是不需道理;我一个人住,点着蜡烛,眼睛模糊;就走破这双鞋,我陪你走一夜……
1
很多时候,我们是凭着内心的信念或是一份自欺的爱情孤独地活着。
但是,有总比无好。至少,那证明我还是我。无论走到哪里,有些痛感虽然自找,但我还能安慰自己:我就是我,不是你眼中的那个我,也不是大街上行色匆匆不苟言笑的那个我。
“上天给了你一株茂盛的身子,所以你只能做一间温暖的树屋!”
我笑。“你呢?康晴是什么意思?”
健康、阳光,多有诗意的名字,我想。
感谢163的风花雪月聊天室!
2
健从死党江那里要到了我的电话号码,回成都第一件事就是给我打电话。
晚上,我赶到河边。临近一看,原来除了健那壮硕的身子外,还有两人。细细一瞅,那女的名蓉,我认识,是江的老婆的唯一闺蜜。她的前男友是河市镇上的一哥,好象还拿过56公斤级散打冠军,听说后来进局子了,也不知是不是真的。
健有点高兴的过了头,一张嘴老半天合不上来。反复地说着得有十年不见了吧,一边不停地劝酒。
三杯啤酒下肚,我脱下外衣。蓉向我端起了杯子,对着我的紧身黑色毛衣瞅了瞅,调笑道:看不出来,你居然有如此发达的胸肌。
健与另一朋友闻言大笑,我只好跟着讪讪地笑。
临走时,健再三叮嘱我没事就给他打电话,常约一处耍。我点头,推着单车欲走,蓉拉住我,问我要电话号码。
“我这儿有,回头我告诉你就是了。”健在一旁招呼道。
3
“树,你不记得我了吗?我是你的女朋友啊!”一个女声嗲声嗲气地在电话那头说道。
“再问一遍,你到底是谁,不回答我立马挂了。”
“莫挂莫挂,是我,前晚一起喝酒的蓉。”
哦,原来是她,我虽然感到略有些意外,但也觉似乎预料之中。毕竟,我所识的女性里,只有她有这种鬼精气了。
蓉在华西院校读书,离着我就几条街的距离。那通电话之后,几乎每晚都喊我陪她出去逛街。我们在她学校的食堂里吃过饭,就出去压马路。从人民南路压到天府广场、春熙路,到合江亭边吹吹府南河的风,在彩虹桥上看看河面泛着灯光的河水。
“我们该不会是在耍朋友吧?”她看着我,鬼里鬼气的一脸坏笑。
我丝毫不以为然。直到一晚从天府广场归来,她突然高声唱起了歌:如果你真的爱我让我走开……一边唱一边伸右手拉住了我的左手。
4
我下定决心不再陪蓉去压马路了。我不喜欢那些在深宵大街上喝醉了酒叫嚣的人,蓉跟他们一样,旁若无人,毫无素养。
“今晚有空吗?来高升桥吃肯德基吧!”
“好啊!”康晴在短信里回道。
一小时后,我在肯德基餐厅里第一次见到了她。中等个子,光洁的额头,大大的眼睛,肤色有股“病态”的白,见面时的一笑多少给我迷惘的心底添了点暖意。
草草结束了一顿并不愉快的晚餐,我骑上单车,戴上耳机,耳朵里再度响起阿杜嘶哑的嗓音:你有多久没有看过那片海,你到现在对自己究竟多明白……
5
“我在七道堰街口等你。”下班前5分钟,蓉在电话里对我说。
在一连三次的回绝之后,她使出了这让我无可推脱的一招。
我知道,一开始我就无意于与她相恋,毕竟同在一个小镇一所中学念书三年,她又是死党老婆的唯一闺蜜——我们不做恋人,我们做兄弟。
我喜欢这样的兄弟!念书时我有好几个“老弟”,都是女孩子。
也许是我自己想多了吧?兄弟牵牵手有何不可呢,说不定人家本没那意思,倒是自己自作多情了呢?
她站在高升大厦门前的拐角街口上,圆圆的脸上开满了暖暖的笑意,跟傍晚乌云密布的天空形成鲜明的对比。
一小时后,大雨倾盆而至。我们在她的学校食堂里吃过饭,她看着我,我看着她,外面豆大的雨点瓢泼也似的下着,显然我们已无处可去。
天已黑透,路灯下的街巷空无一人,几株不甚高大的行道树在大雨中孤零零地耷拉着脑袋,街面上不时越过一辆飞驰的汽车,溅起一滩滩水花。
半小时后,雨滴小了些,但依然毫无停下来的迹象,我起身去推停车棚里的单车。
“你等下,我去给你拿把伞。”
“不用,你拿来我也没法打啊!”我一扭头,她已奔往宿舍而去。
几分钟后,她撑着雨伞走到推着单车的我面前。
我看着她,双手晃了晃单车龙头。她若有所思,忽然恍悟而兴奋地说:“我给你打伞,你载着我!”
6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真愿意这样,我相信自己不是一个在某些方面很随便的人。那么多年一个人走过来,却从未有过寂寞难耐的感觉。
我很清醒:我不可能载着她回到寓所,等雨停后再载着她回来;或者让她自己乘公交或出租车。这显然不是兄弟情义所为,而我寓租的单间只有一张床。
但我没说什么,骑上单车让她打着雨伞坐在了后车架上。
一个生理成熟的正常男人,无论平日在那方面如何清高自律,都依然有着不可抑止的渴望与幻想,我是庸俗的,庸俗到不再去思考今晚以后。
在骑着单车自电信路到战旗小区的途中,我想起何勇在他的歌里大声嘶喊着:我只有一张叽叽喳喳响的床,我骑着单车带你去看夕阳。身后传来蓉愉悦而轻快的歌声: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象花儿开在春风里……
我疑心她在车架上随着歌声的节奏,一摇一荡着自己的腿。这是黎明与曼玉主演的电影《甜蜜蜜》中的情节,曼玉哼着歌,一脸满不在乎的表情,然而幸福,分明写满了整个画面……
7
江打来电话的时候,我刚起床。
“你是不是在跟蓉耍朋友?”他劈头就问。
“这阵子常在一处耍,但我没那意思。”
“没那意思?没那意思就趁早离了她。睡了没?”
“睡了。”
“睡了?那可麻烦了,洁再有一年就出来了,到时不找你对命?再说了,蓉也不是善茬儿,你沾上了怕是脱不了手。”他忧心衷衷。
洁是蓉的男友,河市镇上江湖一哥。进局子前江一直跟他混,合在与江成婚前,仅与江闹过一次掰,那晚江喝得酩酊大醉,洁扶着江在大街上见谁不顺眼就动手,两人情义殊非寻常。
“没事儿,就同床睡了一晚,没那个。”
“吓,你还真忍得住,既然没那个,就没事了。离她远点,免生事端!”江好心告诫我道。
8
江的那通电话以后,我更坚定了不再与蓉交往的想法。
我确定那晚彼此相安无事,在荷尔蒙的作用下,我吻了她。但在吻的那一刻,我突然想到了已是别人妻子的伟。
我们常常会在一份自欺的爱情面前,给自己的心理播下某些自以为信仰的神圣影子。
这影子使我事后深怀侥幸,并隐隐有了些感激。
一周之后,我搬出寓租的屋子。新租的屋子在同一小区的西北角,房间宽敞了许多,楼下街道上在不下雨的夜晚总会飘上些烧烤的味道来。
搬家那天,我通知了健、芳与康晴。
我实在有心撮合健与芳,俩人都奔三了,且都有过一场不幸的婚姻。健看出来了,那天他特别卖力。
中午在街头的小餐馆吃饭的时候,健的电话铃声响了。
“战旗小区,你沿着铁门坎进来,走一百多米就到了。”健开心地说道。
“谁?”我假意问道。
“蓉啊,除了她还有谁?”健笑笑答道。
9
十多分钟以后,蓉站在了我们的桌前。一袭桔黄色T恤上衣,米黄色休闲长裤,照例的齐眉刘海,齐耳短发,圆圆的脸上开满笑意。
显然,她对我刻意视而不见。我能理解,在多次电话回绝之后,她心底一定对我有了些怨气。
“这是芳,家乡人,来自亭子。”健热心地向蓉介绍。
“这是玉,树的朋友。”他指着康晴介绍道。
“是女朋友。”我补充道。康晴满脸笑容地站起身来,向蓉友好地举杯。
“是吗?真好,祝福你们!树,你以前怎么不告诉我?”蓉端起杯中的啤酒,假意地嗔道。
“我们今天才确定恋爱关系呢!”我回答的有些漫不经心。
健留意到蓉除了喝酒几乎没动筷子,拼命给她碗里夹菜。
蓉一直笑容可掬地陪我们吃完午餐。然后起身道别,执拗地说下午还有事,就先走了。
10
晚餐时,健拿出了历练多年的厨子手艺,精心为我们烹制了一桌大餐。看到芳频频的夸奖,我心里暗说有戏。
送走健、芳以后,我和玉面对面看着,心里略有些尴尬。然而玉一脸笑容,看得出来,她很开心。
“我也该走了。”收拾完碗筷后,她笑笑说。
“我送你吧!”我起身奔往卧室去给她拿包。手机突然响了。
蓉打来的。我忐忑地掀开手机盖,按下接听键。
“我一个人在数码广场的阶梯上喝酒,给你半小时,必须过来陪我!”
“来不了,玉还在我这儿呢。”我毫不犹豫地再次亮出玉这块挡箭牌。
“树,实话告诉你,别看我平时疯疯颠颠的没个正形儿,甚至一言不合就跟别人打架,但除了洁之外,你是唯一一个亲吻过我的男人……”
“你必须来,不然我就在这儿坐一晚,我看你能这么狠心不?”
挂了电话,我想起一天到晚嘴上如同念咒语唱Jay歌曲的远。
“你心里到底爱谁?”远在电话那头给我出了一道选择题。
“都不爱。”
“那你不是祸害别人吗?”远的气愤里隐含着一丝身为同事的关心。“那你比较一下,谁在你心里更好一些。”
“自然是玉好些。”我回答道。是的,玉一副温婉可人的样子,丝毫不象容那样个性张扬,以自我为中心。
“那你就得选玉。你必须选,不然就是害了人家。蓉不是喊你过去吗?你就告诉她,你要去也得是带着玉去。”
“你带上玉到她那儿,当着两女孩的面说清楚你心里爱的是玉。说完就带上玉走,不用再理会蓉了。”
靠,这不是影视剧情吗?我心里暗骂远爱情剧看多了,这小鬼头才17岁,说得一套一套的。
可细细一想,好象自己也没什么更好的办法,还真是就这一法子了。
11
蓉的电话再度打来的时候,我告诉她我将带着玉一起过去。说完我就挂了电话,带上玉匆匆奔往小区停车棚而去。
我载着玉一路飞奔到清江东路口时,裤兜里的手机铃声再度响起。
“你到哪里了?”
“清江东路。”
“你一人吗?”
“不,玉在一起。”
“你带着她干什么?”
“我要当着你们的面告诉你,我爱的是她,而不是你!”我的声音大的出奇,玉从身后伸出双手紧紧地搂住了我。
“她是一个好女孩,虽然我才见她一面,但我看得出来……你们不用过来了,我没事,你好好珍惜吧!”蓉的嗓音略带沙哑。
是夜,玉没再提回去。三天后,她携带了一大包行李搬进了我的新居。
12
你要去相信:这世上真的有命这种东西。当你历经人世,懂得认命之时,恰是你告别无知与冲动伊始。
我认命了,伟只是我记忆里的一个符号,或者,只是我对理想爱情的一种精神寄托。这么多年过来,我是在自欺地愚弄着自己要有爱情信仰地活着。
玉看着我在网上码出的文字,一脸幸福。她不知道,那些文字背后,有很多话,是我曾说给心里的伟的。
在我一人独居的那些年,我几乎从不因生活所需而去逛超市。公司里请了保姆专门为我们做工作午餐,一个人的晚餐怎么对付都行,一碗杂酱面,一盘蛋炒饭,一锅米线,一份肥肠粉冒两个结子,照样吃得无比香甜。
玉搬进来后,我们开始为彼此做晚餐。她虽不是出身于什么名门大户,然而我看她切土豆的样子就知道,这是一位自小娇惯的主。
我开始在晚饭后或双休日陪她去逛超市。
我喜欢上青枣的脆与甜,每次逛完超市回来,当她把洗好的青枣端到我面前时,我总会挑出大颗的给她,笑着看她吃完。
13
刘若英的《后来》住进了我们的出租屋,几乎天天响起。穿蓝色百褶裙的女孩,白色的栀子花瓣,高大的院墙边,爬满长青藤的屋檐角下,清新的忧伤划过四周馥郁的空气……在木吉它清亮的音符里,岁月将这一帧影像定格成了玉心中青春的模样。
健与芳同居了,我带着玉隔一周就去芳的寓所一次。我们在一起打打麻将或是斗斗地主,日子飞快地向东流去。
玉也常带我到她唯一的闺蜜红那儿去。我们去新华公园放风筝,在红的出租屋里半夜看鬼片,两个女孩吓得一惊一乍的,往死里捉我与高的胳膊。
记不起哪天开始,我与玉起了争执。她坐在椅上,赌气不睬我。
窗外下着大雨。我走出去,给远打了通电话,冒雨去了就近一家台球室。几局斯洛克打下来,大雨依然滂沱。
玉打过好几通电话给我,我直接挂断,后来干脆关机。
在我心底,固执地认为:这世上如果有一个女孩能在我面前耍脾气,能让我迁就自己去顺从她的心意,只有伟。尽管,她已为别人之妻。
这是一道情锁,来源于我自己。这道锁给了我无比的自由,这自由,来源于我可以因此对其他任何女友的毫不在乎!
是的,我不在乎玉,如果她在我面前耍大小姐脾气,更是一点儿都不!
打完球后,远把带来的雨伞递给我。
“我这儿离家近,你那儿远,路上小心!”他叮嘱道。
当我撑着雨伞快到住处楼下时,我看到楼梯口的大雨里站着一个人。
这人是有病还是怎么着?这么大的雨冒雨淋在雨中舒服吗?我心里暗自嘀咕。
“你到哪里去了,你不知道人家有多担心你吗?”走过人影身边时,她突然开口向我说话。我惊觉她是玉时,她已带着一身淋湿的雨水呜咽着扑进了我的怀里。
14
三个月后,在玉的反复诉苦与房东笑脸消失的前提下,我们搬到了抚琴。
新租屋在一楼,是间二居室屋子。打开后门是块不大的平台,平台下有两步阶梯,阶梯下有一个约六十平米的花园。
这花园,与我们新租的屋子是连在一起的。外面用铁花栅栏隔了开来。花园里有两棵银杏树,一张石桌,四个石凳。
搬过去那天,玉站在满地金黄的银杏树叶中间,伸开双手闭着眼睛原地打起了转。
红和高是这里的常客,健与芳不时过来聚聚,远偶尔也来蹭顿晚餐。
“等我们结婚的时候,买套一楼的房子。要象这样,带一个不大的私家花园!”玉幸福满满地对我说,眼瞳里燃烧着憧憬。
15
“今晚客户请我们聚餐,估计餐后还要去KTV,你自行安排吧!”下班前,我打电话告诉玉。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呢?”玉显然很不高兴。
“不定,总要陪客户尽兴吧!”
我与马俩人为公司完成了一笔不大不小的单,耗时一月,马做设计,我完成理念文本。去掉我与马的工资和奖金,公司净赚十余万。
钱虽不多,但在当时也不算小数目。关键是自接单起,公司根本就没操过心,完全由我们俩自行搞定;更关键的是,客户还分外满意,特意邀请我们会餐并嘱咐餐后一定要K歌尽兴。
皆大欢喜,公司老板、同事人人满面春风。在客户频频举杯的同时,我与马虽然口头一致逊谢着,内心却也颇有志得意满的感觉。
“树,你电话又响了。”马在旁边捅捅我腰。
“你这是怎么了?下班前我不是告诉过你要和客户聚餐吗,这才多一会儿,你都打三个电话了。”我在包间外走廊尽头的窗口冲着电话那头的玉大声斥问道。
“我怕!你不在家,我一个人觉得这屋子好黑好大,后院的花园老是有悉悉梭梭的声音。”
“没什么可怕的,那是风吹树叶的声音。你在家看看电视吧,实在无聊的话你去网吧玩也行!我们还要去K歌呢,回来一定很晚了。你不用等我了!”我的不耐烦略略好了些。
青羊宫旁的“不见不散”KTV豪包里,我唱了两首歌后,手机屏幕再度亮了。
玉是真的胆小害怕,但我对她一再追问我什么时候回去已感到厌烦。或许在她眼里,我现在正在外面高兴玩耍,而忽略了我正在陪客户尽兴这一事实。
男人有很多时候在这种情况下也是工作,但这工作很尴尬:往往家里的女人看到的实质是男人在外面耍。并且这耍的背后,是对她们的不管不顾。
你事业怎么样她根本不关心,她关心的只有一点——你到底有多爱她!
16
20万字的某旅游局导游词一书编写完,我拿到了不长不短的一个假期。
玉在上次的K歌夜闹腾之后,经我语重心长的一番劝告,最近好象消了些性子。忙导游词的时候,加班是常事,她虽然每晚都有电话打来,但好象已刻意控制了自己不会超过三个。
我准备回趟达县,十分想念母亲的家乡红苕粉炒熏制老腊肉。
“这是你的火车票,这张是我的,我们坐位在一起。”玉伸右手向我递出一张票,左手里攥着另一张,满脸笑嘻嘻的神情。
“你不是要上班吗?”
“我已跟老板请了假。正好随你一道去看看叔叔阿姨。”
我看着她手里的车票,无奈地点了点头。
玉在这趟回家的表现不错,进门见到母亲就喊妈妈,帮着母亲做饭洗碗,给父亲点烟沏茶。
“好好珍惜,可别辜负了人家!”临走时,母亲特意叮嘱我。
但我却隐隐感到了害怕。
这辈子,我还未负过任何人。伟虽负了我,但我一点儿也不怨她。我只怨自己,当初与她闹脾气时,为什么就不明白她在自己心中是如此重要!
17
渐渐地,我发现除了上班下班,所有的节假日与下班后的夜晚,玉都会不顾一切地站在我身边。
她从旁边伸过来的手,紧紧地捉住我的胳膊,我常感觉,那是在问我要一份幸福!
星期六的早晨,我去舅家。临走前告诉她,舅有事找我,让她自去红那里玩一天。她不情愿,我对她说,我们能不能给对方一点空间?哪怕只有一天,也好!
当我从停车棚推出单车,正准备上车骑行时,她从后面跑了上来,一下就坐在了后车架上。
我愤怒了,将车随手一扔,毫不理会身后的她与车倒地的声音,大步走了出去。
“她的心理年龄太小了,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爱,应该怎样去爱!”我在路上忿忿地想。
从抚琴一路走到清水河,我用了近一个小时。到舅家门口时,老远就看到舅妈站在家门外。
“你咋这么晚才过来?你们家玉早就到了!”舅妈看着我,热情的招呼道。
偶卖嘎的!进门一抬眼,看见玉正陪着舅开开心心地聊着天。
18
我终于体会到被人黏上了是一种多么不自在的感觉。《大圣娶亲》里猴子冲着黏上来的紫霞龇牙咧嘴,当时我还想:这猴子脑子一定有问题,是啊,带在路上充个取经慰安妇多好!
后来我明白了,你要使她离开你,就必得冲她龇牙咧嘴,因为你心里有愧。
但我每次龇牙以后,却无法再咧嘴。《大圣娶亲》里葡萄反问至尊宝道:爱一个人需要理由吗?需要吗?——那么,爱一个人有错吗?
可我实在受不了她这桎梏一般的爱!所有的休息时间都被她占满了,即使与远、山他们一起玩球的几个小时也不能幸免。
春节终于快到了,我盼望着。她是家里的独女,不回家陪陪父母实在说不过去,我终于可以让自己在这个节假日里彻底地喘口气了。
但我的兴奋只延续了三天半。大年初二下午,当我从外面哼着曲儿回到老家的民房前时,一眼就看到了与母亲正聊得神采飞扬的她。
她居然从四百多公里外的富顺一路风尘仆仆地赶了过来!
我想我明白猴子为什么要对紫霞龇牙咧嘴了——不然他永远成不了猴子!
如果这就是爱,那我宁愿死去也不愿接受。
19
王家卫在《东邪西毒》里说:当你不可以再拥有的时候,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让自己不要忘记。
是的,我从没忘记过。没忘记那一札札起始泛黄的信笺,没忘记那张经岁月冲洗一如初见的脸,她的照片在我随身携带的影集里珍藏着,她的低语依然时时萦绕在我耳边。
我开始对玉的热情冷处理。在她面前,我甚至用刻毒的言语来企图使她自行离开。
她常常在深夜里醒来,大口大口地喘气,泪水自她的眼角滑落到我的颞。
“你不爱我了!”她啜泣着说。
“这世上有很多好男人,但我,是你最不该爱上的那个混蛋!”我在心里默默对她说。
“那我还不如去死!”她对我的沉默显然已无法忍受,裸身滚下床沿,紧接着,我的耳边传来她的头颅碰撞地面的沉闷响声。
我抱起她,看着她的眼睛:“离开我吧,你是一个好女孩,将来一定会生活幸福!”
她悲痛欲绝,眼泪扑簌簌地流了下来……
20
玉的天真在于幻想浪漫,她简单地认为扔掉我影集里伟的照片,就会从我心底抽走对伟的记忆与爱。
但事实是,没有一个男人会忍受这样愚蠢的行为,我自然更不例外!
我常说:一个女人,即令再蠢笨,也不要企图在心爱的男人心里向另两个女人开战——男人的母亲或旧爱。前者无论输赢都陷男人于无地,后者只是一个影子,你打得过么?
我在清江东路找了一个新租屋,二居室的主卧单间,外面有个不大的阳台,另一间屋里租住着三个刚从农大毕业的女孩。
这些天我对玉很好,话也多了许多。给我出主意的那哥们儿说:这些天对她好点,将来自己心里也好受些。
“她不会有事吧?”我很担心。“上次她还拿刀割腕呢!”我补充说。
“没事,放心!只要你不在她身边,她绝对安全,她就是要寻死,也一定要死给你看!”
实说我真没把握!
两天后的清早,我照例起床背包上班。临出门前,我捧起玉的脸,在她的额头吻了吻,转身走了出去。
十多分钟后,在小区门口外的围墙边,我看着玉一脸阳光地出来,向公交站台走去。
确认她不再返回后,我迅速打电话喊来事先约好的一位兄弟,回到屋里匆匆收拾好物什直奔清江东路而去。
21
我给玉留了一床棉被,我带走的一床是化纤的,盖在身上老觉得不舒服。
在清江东路,匆匆放下行李,即与兄弟踏上去雅安的汽车。
这一年多来,她的随时偶然出现让我有如惊弓之鸟。在汽车未过成雅高速收费站之前,我的心一直悬着。
我完全听从了那哥们儿的主意,雅安一周回来后,我换了手机号码,狠心不与远、健他们联系,几有半年。自然,谋食的公司也换了,笋让我跟他一起到二台的某个栏目组做了策划。
新公司的办公楼本来在东门,两月后,突然说要搬到国嘉华庭。见鬼!我心里暗骂。制片人何老师说:要不你每天乘我车上班,走地下车库上办公室。就不会碰见她了。
我已打听清楚:连单元楼、楼幢号都完全一致;所不同的,是玉所在的公司办公楼在二楼,而公司新办公室在三十楼。
“没事儿,我们早上是九点半上班,下午五点半下班,她们一般都是九点上班六点下班,没那么容易撞见。”何老师安慰我道。
22
我战战兢兢地上了一个多星期的班,果然并未撞见过玉。
下午五点,我在楼下的十字路口等笋,到新公司上班后,我们一直形影不离。
远远的,我看到笋正骑着电动自行车晃悠悠出来,便笑着迎上去。
突然,我看到笋背后一个熟悉的身影正推着单车向我这方走来。急忙转身埋头就走,她应该还没发现是我,我心里暗暗盘算着往哪个方向逃。
“树!”笋在我背后大声喊我名字。
“靠,怕啥来啥!”我在心里暗骂鬼运气,我知道笋一定是以为我没看见他。
“树,树!”果然,玉开始跟着大声喊着我的名字,我一回头,看见她弱小的身子推着单车慌不迭地的向我跑来。
“快上来!”笋已发现了情况,在我身前停下车。我慌张地跨上后座,连忙吩咐他:“快跑!”
笋丝毫不理会面前十字路口的红灯已经亮了,载着我火速冲过了路口。
多年以后,我在一篇涂鸦的文字里写道:我们闯红灯,百米冲刺,不可一世的逃亡。
23
我想起玉,想起王家卫在《东邪西毒》里说:如果感情是可以分胜负的话,我不知道她是否会赢。但是我很清楚,从一开始,我就输了。
几年后的一个夜晚,我与远在府河边的一个KTV包间里面对面坐着。
“你知道你走以后把我坑的有多惨吗?”远拧着眉头说。
“她到我家里来找我,问我知道你去了哪里不,反复说起你的好,一说起来就没完没了……”
“她,还好吗?”我似乎有些明知故问。在且听风吟原创文学空间我的文字背后,她曾留言告诉我,她即将结婚。
“很好啊!老公很爱她,她也很满足,自然很幸福了。”
我在心底舒了一口长气!我确定当初的离开是明智之举——男人真爱一个女人,往往会爱一辈子!无论后来的女人怎么温良贤淑,都不可能替代曾经的美好回忆;而女人,尤其是女孩子,当她与你相恋并深爱着你的时候,她愿意为你抛弃一切,但一旦你们分手,她找到继任男友时,却往往比男人更容易转移自己的感情。
因为她们天性向往着浪漫。她们爱上的,只是她们心中认为本来就该怎样轰轰烈烈、怎样风花雪月的爱情本身。你只是在合适的地点合适的时间激活了她们心中的爱情想象,是的,她并不只是爱上了你,她更多爱上的,只是爱情!
责任编辑 苍梧遥
长头发的男人总有一种美,比如年轻时的齐秦,比如《东京爱情故事》里的三上。CD盒封面上的阿杜略侧着脸,几绺发丝随风拂漾着脸庞,似隐含着一丝笑意,眸子里却透着一丝忧伤。
我发了疯地喜欢上他那沙哑的嗓音:ANDY,活着是不需道理;我一个人住,点着蜡烛,眼睛模糊;就走破这双鞋,我陪你走一夜……
1
很多时候,我们是凭着内心的信念或是一份自欺的爱情孤独地活着。
但是,有总比无好。至少,那证明我还是我。无论走到哪里,有些痛感虽然自找,但我还能安慰自己:我就是我,不是你眼中的那个我,也不是大街上行色匆匆不苟言笑的那个我。
“上天给了你一株茂盛的身子,所以你只能做一间温暖的树屋!”
我笑。“你呢?康晴是什么意思?”
健康、阳光,多有诗意的名字,我想。
感谢163的风花雪月聊天室!
2
健从死党江那里要到了我的电话号码,回成都第一件事就是给我打电话。
晚上,我赶到河边。临近一看,原来除了健那壮硕的身子外,还有两人。细细一瞅,那女的名蓉,我认识,是江的老婆的唯一闺蜜。她的前男友是河市镇上的一哥,好象还拿过56公斤级散打冠军,听说后来进局子了,也不知是不是真的。
健有点高兴的过了头,一张嘴老半天合不上来。反复地说着得有十年不见了吧,一边不停地劝酒。
三杯啤酒下肚,我脱下外衣。蓉向我端起了杯子,对着我的紧身黑色毛衣瞅了瞅,调笑道:看不出来,你居然有如此发达的胸肌。
健与另一朋友闻言大笑,我只好跟着讪讪地笑。
临走时,健再三叮嘱我没事就给他打电话,常约一处耍。我点头,推着单车欲走,蓉拉住我,问我要电话号码。
“我这儿有,回头我告诉你就是了。”健在一旁招呼道。
3
“树,你不记得我了吗?我是你的女朋友啊!”一个女声嗲声嗲气地在电话那头说道。
“再问一遍,你到底是谁,不回答我立马挂了。”
“莫挂莫挂,是我,前晚一起喝酒的蓉。”
哦,原来是她,我虽然感到略有些意外,但也觉似乎预料之中。毕竟,我所识的女性里,只有她有这种鬼精气了。
蓉在华西院校读书,离着我就几条街的距离。那通电话之后,几乎每晚都喊我陪她出去逛街。我们在她学校的食堂里吃过饭,就出去压马路。从人民南路压到天府广场、春熙路,到合江亭边吹吹府南河的风,在彩虹桥上看看河面泛着灯光的河水。
“我们该不会是在耍朋友吧?”她看着我,鬼里鬼气的一脸坏笑。
我丝毫不以为然。直到一晚从天府广场归来,她突然高声唱起了歌:如果你真的爱我让我走开……一边唱一边伸右手拉住了我的左手。
4
我下定决心不再陪蓉去压马路了。我不喜欢那些在深宵大街上喝醉了酒叫嚣的人,蓉跟他们一样,旁若无人,毫无素养。
“今晚有空吗?来高升桥吃肯德基吧!”
“好啊!”康晴在短信里回道。
一小时后,我在肯德基餐厅里第一次见到了她。中等个子,光洁的额头,大大的眼睛,肤色有股“病态”的白,见面时的一笑多少给我迷惘的心底添了点暖意。
草草结束了一顿并不愉快的晚餐,我骑上单车,戴上耳机,耳朵里再度响起阿杜嘶哑的嗓音:你有多久没有看过那片海,你到现在对自己究竟多明白……
5
“我在七道堰街口等你。”下班前5分钟,蓉在电话里对我说。
在一连三次的回绝之后,她使出了这让我无可推脱的一招。
我知道,一开始我就无意于与她相恋,毕竟同在一个小镇一所中学念书三年,她又是死党老婆的唯一闺蜜——我们不做恋人,我们做兄弟。
我喜欢这样的兄弟!念书时我有好几个“老弟”,都是女孩子。
也许是我自己想多了吧?兄弟牵牵手有何不可呢,说不定人家本没那意思,倒是自己自作多情了呢?
她站在高升大厦门前的拐角街口上,圆圆的脸上开满了暖暖的笑意,跟傍晚乌云密布的天空形成鲜明的对比。
一小时后,大雨倾盆而至。我们在她的学校食堂里吃过饭,她看着我,我看着她,外面豆大的雨点瓢泼也似的下着,显然我们已无处可去。
天已黑透,路灯下的街巷空无一人,几株不甚高大的行道树在大雨中孤零零地耷拉着脑袋,街面上不时越过一辆飞驰的汽车,溅起一滩滩水花。
半小时后,雨滴小了些,但依然毫无停下来的迹象,我起身去推停车棚里的单车。
“你等下,我去给你拿把伞。”
“不用,你拿来我也没法打啊!”我一扭头,她已奔往宿舍而去。
几分钟后,她撑着雨伞走到推着单车的我面前。
我看着她,双手晃了晃单车龙头。她若有所思,忽然恍悟而兴奋地说:“我给你打伞,你载着我!”
6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真愿意这样,我相信自己不是一个在某些方面很随便的人。那么多年一个人走过来,却从未有过寂寞难耐的感觉。
我很清醒:我不可能载着她回到寓所,等雨停后再载着她回来;或者让她自己乘公交或出租车。这显然不是兄弟情义所为,而我寓租的单间只有一张床。
但我没说什么,骑上单车让她打着雨伞坐在了后车架上。
一个生理成熟的正常男人,无论平日在那方面如何清高自律,都依然有着不可抑止的渴望与幻想,我是庸俗的,庸俗到不再去思考今晚以后。
在骑着单车自电信路到战旗小区的途中,我想起何勇在他的歌里大声嘶喊着:我只有一张叽叽喳喳响的床,我骑着单车带你去看夕阳。身后传来蓉愉悦而轻快的歌声: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象花儿开在春风里……
我疑心她在车架上随着歌声的节奏,一摇一荡着自己的腿。这是黎明与曼玉主演的电影《甜蜜蜜》中的情节,曼玉哼着歌,一脸满不在乎的表情,然而幸福,分明写满了整个画面……
7
江打来电话的时候,我刚起床。
“你是不是在跟蓉耍朋友?”他劈头就问。
“这阵子常在一处耍,但我没那意思。”
“没那意思?没那意思就趁早离了她。睡了没?”
“睡了。”
“睡了?那可麻烦了,洁再有一年就出来了,到时不找你对命?再说了,蓉也不是善茬儿,你沾上了怕是脱不了手。”他忧心衷衷。
洁是蓉的男友,河市镇上江湖一哥。进局子前江一直跟他混,合在与江成婚前,仅与江闹过一次掰,那晚江喝得酩酊大醉,洁扶着江在大街上见谁不顺眼就动手,两人情义殊非寻常。
“没事儿,就同床睡了一晚,没那个。”
“吓,你还真忍得住,既然没那个,就没事了。离她远点,免生事端!”江好心告诫我道。
8
江的那通电话以后,我更坚定了不再与蓉交往的想法。
我确定那晚彼此相安无事,在荷尔蒙的作用下,我吻了她。但在吻的那一刻,我突然想到了已是别人妻子的伟。
我们常常会在一份自欺的爱情面前,给自己的心理播下某些自以为信仰的神圣影子。
这影子使我事后深怀侥幸,并隐隐有了些感激。
一周之后,我搬出寓租的屋子。新租的屋子在同一小区的西北角,房间宽敞了许多,楼下街道上在不下雨的夜晚总会飘上些烧烤的味道来。
搬家那天,我通知了健、芳与康晴。
我实在有心撮合健与芳,俩人都奔三了,且都有过一场不幸的婚姻。健看出来了,那天他特别卖力。
中午在街头的小餐馆吃饭的时候,健的电话铃声响了。
“战旗小区,你沿着铁门坎进来,走一百多米就到了。”健开心地说道。
“谁?”我假意问道。
“蓉啊,除了她还有谁?”健笑笑答道。
9
十多分钟以后,蓉站在了我们的桌前。一袭桔黄色T恤上衣,米黄色休闲长裤,照例的齐眉刘海,齐耳短发,圆圆的脸上开满笑意。
显然,她对我刻意视而不见。我能理解,在多次电话回绝之后,她心底一定对我有了些怨气。
“这是芳,家乡人,来自亭子。”健热心地向蓉介绍。
“这是玉,树的朋友。”他指着康晴介绍道。
“是女朋友。”我补充道。康晴满脸笑容地站起身来,向蓉友好地举杯。
“是吗?真好,祝福你们!树,你以前怎么不告诉我?”蓉端起杯中的啤酒,假意地嗔道。
“我们今天才确定恋爱关系呢!”我回答的有些漫不经心。
健留意到蓉除了喝酒几乎没动筷子,拼命给她碗里夹菜。
蓉一直笑容可掬地陪我们吃完午餐。然后起身道别,执拗地说下午还有事,就先走了。
10
晚餐时,健拿出了历练多年的厨子手艺,精心为我们烹制了一桌大餐。看到芳频频的夸奖,我心里暗说有戏。
送走健、芳以后,我和玉面对面看着,心里略有些尴尬。然而玉一脸笑容,看得出来,她很开心。
“我也该走了。”收拾完碗筷后,她笑笑说。
“我送你吧!”我起身奔往卧室去给她拿包。手机突然响了。
蓉打来的。我忐忑地掀开手机盖,按下接听键。
“我一个人在数码广场的阶梯上喝酒,给你半小时,必须过来陪我!”
“来不了,玉还在我这儿呢。”我毫不犹豫地再次亮出玉这块挡箭牌。
“树,实话告诉你,别看我平时疯疯颠颠的没个正形儿,甚至一言不合就跟别人打架,但除了洁之外,你是唯一一个亲吻过我的男人……”
“你必须来,不然我就在这儿坐一晚,我看你能这么狠心不?”
挂了电话,我想起一天到晚嘴上如同念咒语唱Jay歌曲的远。
“你心里到底爱谁?”远在电话那头给我出了一道选择题。
“都不爱。”
“那你不是祸害别人吗?”远的气愤里隐含着一丝身为同事的关心。“那你比较一下,谁在你心里更好一些。”
“自然是玉好些。”我回答道。是的,玉一副温婉可人的样子,丝毫不象容那样个性张扬,以自我为中心。
“那你就得选玉。你必须选,不然就是害了人家。蓉不是喊你过去吗?你就告诉她,你要去也得是带着玉去。”
“你带上玉到她那儿,当着两女孩的面说清楚你心里爱的是玉。说完就带上玉走,不用再理会蓉了。”
靠,这不是影视剧情吗?我心里暗骂远爱情剧看多了,这小鬼头才17岁,说得一套一套的。
可细细一想,好象自己也没什么更好的办法,还真是就这一法子了。
11
蓉的电话再度打来的时候,我告诉她我将带着玉一起过去。说完我就挂了电话,带上玉匆匆奔往小区停车棚而去。
我载着玉一路飞奔到清江东路口时,裤兜里的手机铃声再度响起。
“你到哪里了?”
“清江东路。”
“你一人吗?”
“不,玉在一起。”
“你带着她干什么?”
“我要当着你们的面告诉你,我爱的是她,而不是你!”我的声音大的出奇,玉从身后伸出双手紧紧地搂住了我。
“她是一个好女孩,虽然我才见她一面,但我看得出来……你们不用过来了,我没事,你好好珍惜吧!”蓉的嗓音略带沙哑。
是夜,玉没再提回去。三天后,她携带了一大包行李搬进了我的新居。
12
你要去相信:这世上真的有命这种东西。当你历经人世,懂得认命之时,恰是你告别无知与冲动伊始。
我认命了,伟只是我记忆里的一个符号,或者,只是我对理想爱情的一种精神寄托。这么多年过来,我是在自欺地愚弄着自己要有爱情信仰地活着。
玉看着我在网上码出的文字,一脸幸福。她不知道,那些文字背后,有很多话,是我曾说给心里的伟的。
在我一人独居的那些年,我几乎从不因生活所需而去逛超市。公司里请了保姆专门为我们做工作午餐,一个人的晚餐怎么对付都行,一碗杂酱面,一盘蛋炒饭,一锅米线,一份肥肠粉冒两个结子,照样吃得无比香甜。
玉搬进来后,我们开始为彼此做晚餐。她虽不是出身于什么名门大户,然而我看她切土豆的样子就知道,这是一位自小娇惯的主。
我开始在晚饭后或双休日陪她去逛超市。
我喜欢上青枣的脆与甜,每次逛完超市回来,当她把洗好的青枣端到我面前时,我总会挑出大颗的给她,笑着看她吃完。
13
刘若英的《后来》住进了我们的出租屋,几乎天天响起。穿蓝色百褶裙的女孩,白色的栀子花瓣,高大的院墙边,爬满长青藤的屋檐角下,清新的忧伤划过四周馥郁的空气……在木吉它清亮的音符里,岁月将这一帧影像定格成了玉心中青春的模样。
健与芳同居了,我带着玉隔一周就去芳的寓所一次。我们在一起打打麻将或是斗斗地主,日子飞快地向东流去。
玉也常带我到她唯一的闺蜜红那儿去。我们去新华公园放风筝,在红的出租屋里半夜看鬼片,两个女孩吓得一惊一乍的,往死里捉我与高的胳膊。
记不起哪天开始,我与玉起了争执。她坐在椅上,赌气不睬我。
窗外下着大雨。我走出去,给远打了通电话,冒雨去了就近一家台球室。几局斯洛克打下来,大雨依然滂沱。
玉打过好几通电话给我,我直接挂断,后来干脆关机。
在我心底,固执地认为:这世上如果有一个女孩能在我面前耍脾气,能让我迁就自己去顺从她的心意,只有伟。尽管,她已为别人之妻。
这是一道情锁,来源于我自己。这道锁给了我无比的自由,这自由,来源于我可以因此对其他任何女友的毫不在乎!
是的,我不在乎玉,如果她在我面前耍大小姐脾气,更是一点儿都不!
打完球后,远把带来的雨伞递给我。
“我这儿离家近,你那儿远,路上小心!”他叮嘱道。
当我撑着雨伞快到住处楼下时,我看到楼梯口的大雨里站着一个人。
这人是有病还是怎么着?这么大的雨冒雨淋在雨中舒服吗?我心里暗自嘀咕。
“你到哪里去了,你不知道人家有多担心你吗?”走过人影身边时,她突然开口向我说话。我惊觉她是玉时,她已带着一身淋湿的雨水呜咽着扑进了我的怀里。
14
三个月后,在玉的反复诉苦与房东笑脸消失的前提下,我们搬到了抚琴。
新租屋在一楼,是间二居室屋子。打开后门是块不大的平台,平台下有两步阶梯,阶梯下有一个约六十平米的花园。
这花园,与我们新租的屋子是连在一起的。外面用铁花栅栏隔了开来。花园里有两棵银杏树,一张石桌,四个石凳。
搬过去那天,玉站在满地金黄的银杏树叶中间,伸开双手闭着眼睛原地打起了转。
红和高是这里的常客,健与芳不时过来聚聚,远偶尔也来蹭顿晚餐。
“等我们结婚的时候,买套一楼的房子。要象这样,带一个不大的私家花园!”玉幸福满满地对我说,眼瞳里燃烧着憧憬。
15
“今晚客户请我们聚餐,估计餐后还要去KTV,你自行安排吧!”下班前,我打电话告诉玉。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呢?”玉显然很不高兴。
“不定,总要陪客户尽兴吧!”
我与马俩人为公司完成了一笔不大不小的单,耗时一月,马做设计,我完成理念文本。去掉我与马的工资和奖金,公司净赚十余万。
钱虽不多,但在当时也不算小数目。关键是自接单起,公司根本就没操过心,完全由我们俩自行搞定;更关键的是,客户还分外满意,特意邀请我们会餐并嘱咐餐后一定要K歌尽兴。
皆大欢喜,公司老板、同事人人满面春风。在客户频频举杯的同时,我与马虽然口头一致逊谢着,内心却也颇有志得意满的感觉。
“树,你电话又响了。”马在旁边捅捅我腰。
“你这是怎么了?下班前我不是告诉过你要和客户聚餐吗,这才多一会儿,你都打三个电话了。”我在包间外走廊尽头的窗口冲着电话那头的玉大声斥问道。
“我怕!你不在家,我一个人觉得这屋子好黑好大,后院的花园老是有悉悉梭梭的声音。”
“没什么可怕的,那是风吹树叶的声音。你在家看看电视吧,实在无聊的话你去网吧玩也行!我们还要去K歌呢,回来一定很晚了。你不用等我了!”我的不耐烦略略好了些。
青羊宫旁的“不见不散”KTV豪包里,我唱了两首歌后,手机屏幕再度亮了。
玉是真的胆小害怕,但我对她一再追问我什么时候回去已感到厌烦。或许在她眼里,我现在正在外面高兴玩耍,而忽略了我正在陪客户尽兴这一事实。
男人有很多时候在这种情况下也是工作,但这工作很尴尬:往往家里的女人看到的实质是男人在外面耍。并且这耍的背后,是对她们的不管不顾。
你事业怎么样她根本不关心,她关心的只有一点——你到底有多爱她!
16
20万字的某旅游局导游词一书编写完,我拿到了不长不短的一个假期。
玉在上次的K歌夜闹腾之后,经我语重心长的一番劝告,最近好象消了些性子。忙导游词的时候,加班是常事,她虽然每晚都有电话打来,但好象已刻意控制了自己不会超过三个。
我准备回趟达县,十分想念母亲的家乡红苕粉炒熏制老腊肉。
“这是你的火车票,这张是我的,我们坐位在一起。”玉伸右手向我递出一张票,左手里攥着另一张,满脸笑嘻嘻的神情。
“你不是要上班吗?”
“我已跟老板请了假。正好随你一道去看看叔叔阿姨。”
我看着她手里的车票,无奈地点了点头。
玉在这趟回家的表现不错,进门见到母亲就喊妈妈,帮着母亲做饭洗碗,给父亲点烟沏茶。
“好好珍惜,可别辜负了人家!”临走时,母亲特意叮嘱我。
但我却隐隐感到了害怕。
这辈子,我还未负过任何人。伟虽负了我,但我一点儿也不怨她。我只怨自己,当初与她闹脾气时,为什么就不明白她在自己心中是如此重要!
17
渐渐地,我发现除了上班下班,所有的节假日与下班后的夜晚,玉都会不顾一切地站在我身边。
她从旁边伸过来的手,紧紧地捉住我的胳膊,我常感觉,那是在问我要一份幸福!
星期六的早晨,我去舅家。临走前告诉她,舅有事找我,让她自去红那里玩一天。她不情愿,我对她说,我们能不能给对方一点空间?哪怕只有一天,也好!
当我从停车棚推出单车,正准备上车骑行时,她从后面跑了上来,一下就坐在了后车架上。
我愤怒了,将车随手一扔,毫不理会身后的她与车倒地的声音,大步走了出去。
“她的心理年龄太小了,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爱,应该怎样去爱!”我在路上忿忿地想。
从抚琴一路走到清水河,我用了近一个小时。到舅家门口时,老远就看到舅妈站在家门外。
“你咋这么晚才过来?你们家玉早就到了!”舅妈看着我,热情的招呼道。
偶卖嘎的!进门一抬眼,看见玉正陪着舅开开心心地聊着天。
18
我终于体会到被人黏上了是一种多么不自在的感觉。《大圣娶亲》里猴子冲着黏上来的紫霞龇牙咧嘴,当时我还想:这猴子脑子一定有问题,是啊,带在路上充个取经慰安妇多好!
后来我明白了,你要使她离开你,就必得冲她龇牙咧嘴,因为你心里有愧。
但我每次龇牙以后,却无法再咧嘴。《大圣娶亲》里葡萄反问至尊宝道:爱一个人需要理由吗?需要吗?——那么,爱一个人有错吗?
可我实在受不了她这桎梏一般的爱!所有的休息时间都被她占满了,即使与远、山他们一起玩球的几个小时也不能幸免。
春节终于快到了,我盼望着。她是家里的独女,不回家陪陪父母实在说不过去,我终于可以让自己在这个节假日里彻底地喘口气了。
但我的兴奋只延续了三天半。大年初二下午,当我从外面哼着曲儿回到老家的民房前时,一眼就看到了与母亲正聊得神采飞扬的她。
她居然从四百多公里外的富顺一路风尘仆仆地赶了过来!
我想我明白猴子为什么要对紫霞龇牙咧嘴了——不然他永远成不了猴子!
如果这就是爱,那我宁愿死去也不愿接受。
19
王家卫在《东邪西毒》里说:当你不可以再拥有的时候,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让自己不要忘记。
是的,我从没忘记过。没忘记那一札札起始泛黄的信笺,没忘记那张经岁月冲洗一如初见的脸,她的照片在我随身携带的影集里珍藏着,她的低语依然时时萦绕在我耳边。
我开始对玉的热情冷处理。在她面前,我甚至用刻毒的言语来企图使她自行离开。
她常常在深夜里醒来,大口大口地喘气,泪水自她的眼角滑落到我的颞。
“你不爱我了!”她啜泣着说。
“这世上有很多好男人,但我,是你最不该爱上的那个混蛋!”我在心里默默对她说。
“那我还不如去死!”她对我的沉默显然已无法忍受,裸身滚下床沿,紧接着,我的耳边传来她的头颅碰撞地面的沉闷响声。
我抱起她,看着她的眼睛:“离开我吧,你是一个好女孩,将来一定会生活幸福!”
她悲痛欲绝,眼泪扑簌簌地流了下来……
20
玉的天真在于幻想浪漫,她简单地认为扔掉我影集里伟的照片,就会从我心底抽走对伟的记忆与爱。
但事实是,没有一个男人会忍受这样愚蠢的行为,我自然更不例外!
我常说:一个女人,即令再蠢笨,也不要企图在心爱的男人心里向另两个女人开战——男人的母亲或旧爱。前者无论输赢都陷男人于无地,后者只是一个影子,你打得过么?
我在清江东路找了一个新租屋,二居室的主卧单间,外面有个不大的阳台,另一间屋里租住着三个刚从农大毕业的女孩。
这些天我对玉很好,话也多了许多。给我出主意的那哥们儿说:这些天对她好点,将来自己心里也好受些。
“她不会有事吧?”我很担心。“上次她还拿刀割腕呢!”我补充说。
“没事,放心!只要你不在她身边,她绝对安全,她就是要寻死,也一定要死给你看!”
实说我真没把握!
两天后的清早,我照例起床背包上班。临出门前,我捧起玉的脸,在她的额头吻了吻,转身走了出去。
十多分钟后,在小区门口外的围墙边,我看着玉一脸阳光地出来,向公交站台走去。
确认她不再返回后,我迅速打电话喊来事先约好的一位兄弟,回到屋里匆匆收拾好物什直奔清江东路而去。
21
我给玉留了一床棉被,我带走的一床是化纤的,盖在身上老觉得不舒服。
在清江东路,匆匆放下行李,即与兄弟踏上去雅安的汽车。
这一年多来,她的随时偶然出现让我有如惊弓之鸟。在汽车未过成雅高速收费站之前,我的心一直悬着。
我完全听从了那哥们儿的主意,雅安一周回来后,我换了手机号码,狠心不与远、健他们联系,几有半年。自然,谋食的公司也换了,笋让我跟他一起到二台的某个栏目组做了策划。
新公司的办公楼本来在东门,两月后,突然说要搬到国嘉华庭。见鬼!我心里暗骂。制片人何老师说:要不你每天乘我车上班,走地下车库上办公室。就不会碰见她了。
我已打听清楚:连单元楼、楼幢号都完全一致;所不同的,是玉所在的公司办公楼在二楼,而公司新办公室在三十楼。
“没事儿,我们早上是九点半上班,下午五点半下班,她们一般都是九点上班六点下班,没那么容易撞见。”何老师安慰我道。
22
我战战兢兢地上了一个多星期的班,果然并未撞见过玉。
下午五点,我在楼下的十字路口等笋,到新公司上班后,我们一直形影不离。
远远的,我看到笋正骑着电动自行车晃悠悠出来,便笑着迎上去。
突然,我看到笋背后一个熟悉的身影正推着单车向我这方走来。急忙转身埋头就走,她应该还没发现是我,我心里暗暗盘算着往哪个方向逃。
“树!”笋在我背后大声喊我名字。
“靠,怕啥来啥!”我在心里暗骂鬼运气,我知道笋一定是以为我没看见他。
“树,树!”果然,玉开始跟着大声喊着我的名字,我一回头,看见她弱小的身子推着单车慌不迭地的向我跑来。
“快上来!”笋已发现了情况,在我身前停下车。我慌张地跨上后座,连忙吩咐他:“快跑!”
笋丝毫不理会面前十字路口的红灯已经亮了,载着我火速冲过了路口。
多年以后,我在一篇涂鸦的文字里写道:我们闯红灯,百米冲刺,不可一世的逃亡。
23
我想起玉,想起王家卫在《东邪西毒》里说:如果感情是可以分胜负的话,我不知道她是否会赢。但是我很清楚,从一开始,我就输了。
几年后的一个夜晚,我与远在府河边的一个KTV包间里面对面坐着。
“你知道你走以后把我坑的有多惨吗?”远拧着眉头说。
“她到我家里来找我,问我知道你去了哪里不,反复说起你的好,一说起来就没完没了……”
“她,还好吗?”我似乎有些明知故问。在且听风吟原创文学空间我的文字背后,她曾留言告诉我,她即将结婚。
“很好啊!老公很爱她,她也很满足,自然很幸福了。”
我在心底舒了一口长气!我确定当初的离开是明智之举——男人真爱一个女人,往往会爱一辈子!无论后来的女人怎么温良贤淑,都不可能替代曾经的美好回忆;而女人,尤其是女孩子,当她与你相恋并深爱着你的时候,她愿意为你抛弃一切,但一旦你们分手,她找到继任男友时,却往往比男人更容易转移自己的感情。
因为她们天性向往着浪漫。她们爱上的,只是她们心中认为本来就该怎样轰轰烈烈、怎样风花雪月的爱情本身。你只是在合适的地点合适的时间激活了她们心中的爱情想象,是的,她并不只是爱上了你,她更多爱上的,只是爱情!
责任编辑 苍梧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