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明老茶
老家的烟囱歪斜着从灶膛通向屋顶。不仅我的老家,乡村里的农舍很多是这样子,烟囱拱出黑瓦,在瓦槽间突起约两尺高。家里每次生火做饭,浓烟就从那里喷涌而出,白色的烟雾携带着一家子的温暖冲向天空,一会儿就融入天色中。从天空高处收回目光,在黑瓦之下,高出灶台两米多的烟囱中段圈着一圈铁线,一根麻绳系着一个包包吊在铁线圈上。这里说明一下,农家老灶台的烟囱一般是嵌入式的,循着灶台靠墙挖出一条竖直的沟,在屋顶部垒个烟囱,屋里是看不见烟筒的。而我家的这个灶台位置经历了几次挪移,最后选定在不靠墙的天井边,因此,烟囱只能用约两尺长的烟筒一节一节连接起来,外围三面用三支一丈多长的竹片围拢绑定,形成了这个外露式的烟囱。
那个包包显然很有一些时日了,像祖母床上的那个枕头一样黑乎乎的,两块砖头那么厚,外边包装的纸沾满灶台烟灰,烟灰又长出胡须,完全看不出纸张的色彩。灶膛生火时,如果火势太旺,烟囱排不出去,就会从灶膛口涌出火舌,鼓动着灶间的空气,“烟灰的胡须”就会随之微微摆动。一开始我不知道那是什么,直到有一天母亲见我的小眼睛盯着它看,就说那是清明茶,吃了清凉退火的,放很多年了,很久没有动过了。母亲在“清凉退火”这个词语面前加了个词语“头号”。母亲说这话的语气有些郑重,有些自豪,总之很宝贝的样子。
小时候的老家盛产茶叶,屋后山,村前山,河对面山上,到处是小队的或是大队的茶园,我们山里娃年纪很小就跟着大人上山采茶,挣工分,虽然公分少得可怜,采茶的数量根本无法与大人比,乐趣只在于可以满山乱窜。虽然自小就接触茶园,也目睹了大人们在小队址集体制茶的情景,但是,对清明茶却知之甚少。
十六岁那年的一个周末,我带着满嘴的泡泡从寄宿学校火急火燎地回到家里,母亲两手扯着我的嘴巴左瞧瞧右瞧瞧,说:“不着急不着急!泡一碗清明茶就好了。”
那正是黄昏时候,还没生火煮饭,母亲叫我爬上灶台,把那个包包解下来。我发现那包包外层不知啥时候又用蓆草(织草席的草)再捆扎过一遍,显见原先的麻绳年深日久自然断开了。包包拿下来,母亲接过去,走到天井里吹了吹面上的烟灰,那烟灰却不为所动,只好用抹布先擦一遍,再放在簸箕上。解开席草,纸张却早已经失去柔韧度,一碰就破,像是白皮饼。外层是报纸,报纸内面的色彩焦黄,字迹却十分立体清楚。抖落不堪一碰的报纸,露出里层,是又一重农村人习惯称之为“粗纸”?的,黄色,表面粗糙,人们最常用它来包裹茶叶,理由据说是这种纸张没有杂味。粗纸也已经失去了弹性,像干枯的硬硬的树叶。母亲掀开这重重包裹,终于露出了庐山真面目:清明茶,粗看是黑色的,细看却在黑、红、褐之间,表面有一层白色的菌毛似的东西,其实那又不是菌毛,是茶叶存放久了自然呈现的一种色泽。俯身用鼻子去闻,有一种似霉味又不像霉味的味道发散着。
“这可是我还年轻的时候就采摘的清明茶,比你的年纪还大,以前很大包的,现在就剩这些了。”
母亲撮了一小撮这些宝贝放进铝制小茶壶,用木瓢舀了在锅里沸腾的开水灌进去,马上倒掉第一遍茶汤。茶汤冲击在天井的石面上,突突突作响。再舀一瓢开水倒进茶壶,母亲说:“让它浸泡一下,待会儿再倒出来喝”。
就在我等待的时候,父亲扛着锄头从门外回来了,脚上还湿漉漉的,他习惯在房前的水坑把田里干活时沾上的泥土洗干净再回家。他看见还敞开着的清明茶,就赶忙用汗巾擦一把手,走进里间,不知从哪个角落翻出一张牛皮纸。牛皮纸肯定是包过别的什么东西,此刻翻出来是重复使用。父亲使劲抖了抖牛皮纸,吹了吹纸面,铺在簸箕一角,小心翼翼捧起清明茶,移到牛皮纸上面,先从三面将清明茶包成方形筒状,在簸箕上顿了又顿,最后结结实实地包好。照例,外层还是加上一重报纸,我知道,那些报纸都是从大队部捎回来的。
“等一会你妈饭做好了,再把它重新吊上去,放在那上面才好保存,”父亲说,“这清明茶很耐泡,你这一泡现在可以倒出来喝了,再冲些开水继续浸泡着,还很浓。”
拎起茶壶倒茶,从壶嘴到碗里,这一段短短的距离,茶汤演绎了一段短短的乌龙的形象。茶色浓得像酱油,看着是红的,红中透着黄,恍惚看着似乎又有一点黑,茶汤面上浮动着一层白色,像气雾,像茸毛。我端着茶碗,凑近嘴边轻轻吹着,白色的气雾散开了又聚拢,还是那种似霉味又不是霉味的气味率先涌进了鼻孔。那是一种岁月沧桑的味道,说不清道不明的一种成熟的滋味,不呛,不香。我们山村里的人,习惯于把清明茶的茶汤说成牛尿,的确,这茶汤太像牛尿了,仅从气味来说,它可是一丁点也不吸引人。但是,从大人们平日里的谈话聊天当中知道,清明茶很早就被山村的人们当做宝贝用着,除了清凉去火,加点盐还可以消炎止泻。
茶汤凉下来了,轻轻吮吸一口,苦苦的,夹杂着火烧火燎过的焦味。焦苦味的后头紧跟而来的是甘,绵绵的,醇醇的,想着母亲的“清明茶最是清凉退火”的交代,于是大口一饮而净,等到茶水尽数滑过喉咙,便只剩下舌底生津了。我想,老家的清明茶如果真是宝贝的话,那么它也是含蓄的,一点也不张扬。
重新爬回烟囱上面的这一包清明茶,穿上新衣服而特别显眼,与那黑漆漆的烟囱形成强烈的对比。灶膛口涌出的烟雾熏着它,不久它的外衣将再次变得乌黑。
晚饭的时候,母亲见我吃饭吞咽困难的样子,就很肯定地说,明天火气就没了。至于第二天我的口舌之火是否退去,我还真是记不得了,只知道那包清明茶一直陪伴着烟囱,直到我高考那年,录取之前,父亲把它拆分了,分头送给了城里人。而清明前后采摘、并因之而得名的清明茶,它长在茶树上的样子一直到我年逾半百之后,才在一次采访过程中,在老家的红军洞前见到,因为山地开发的缘故,原本漫山遍野的清明茶树被欺凌得只剩下孤零零的一株,树干有手臂那么粗,直通通地耸向天空,停止在老家烟囱的高度,树梢叶子稀稀疏疏,在山风中摇摆着,像是与天空招手,又像是挥手道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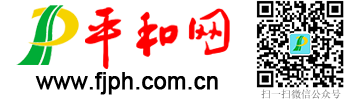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