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棵龙眼树
几个朋友一块儿喝茶聊天,聊着聊着又聊到了各自儿时的快乐时光。凤说她家兔子养得多,她的快乐离不开兔子;玉说她的快乐是骑在牛背上;云说她家的7棵龙眼树是她满满的回忆;我说,我家也有两棵龙眼树,小时候,这两棵龙眼树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快乐与希望。
我家的两棵龙眼树种在我们居住的土楼后面。当我记事起,这两棵龙眼树已经很老了,有二三层楼高,很茂盛,估计是爷爷年轻的时候种下的。一大一小两棵龙眼树相距10来米,小的那棵树干我一人能合抱,大的那棵我们三姐妹手拉手还合抱不过来。树干皱皱巴巴的,就像饱经风霜的百岁老人脸上的皱纹,又像鳄鱼皮,那凸起的树疙瘩像怒视的眼睛,有时会让人恍惚有几只鳄鱼趴在树干上一动不动地瞪着眼睛注视你,一贯胆小如鼠的我偶尔自己路过,还不敢正视树干一眼,赶紧快步离开。枝干夸张地向四周伸展,叶子挨挨挤挤的,绿得深沉、绿得发亮。当暴风骤雨来时,狂风吹得它满树绿叶犹如一头发怒的雄狮,翻卷着咆哮着,它总是顽强地抵挡狂风暴雨的肆意摧残。它始终岿然不动伫立于屋后,在风雨中欢笑,在晴空里歌唱,把全土楼人的甜酸苦辣都记载进它的摇曳中。
春天来了,沉寂了一冬的龙眼树慢慢地苏醒过来,它在斜风细雨中抖落残冬留下的斑斑痕迹,贪婪地吮吸着亚热带温暖的阳光、雨露,舒展开淡绿色的枝条,吐露粉红的嫩芽。抬头看,那嫩红色的叶片儿在绿叶中伸展,就像刚刚出生的婴儿那般粉嫩,不禁让人产生怜爱之心。远远望去,又像一把绿底红顶大花伞便撑得特别引人注目了。
初夏,龙眼树开花了。龙眼的花很小,形状和颜色都有点像小绿豆,但体积比小绿豆还小。那一串串淡黄色的细碎花朵散发出来的淡淡清香,招蝴蝶翩翩起舞,引蜜蜂嗡嗡传授花粉。这个时候,就会发现离龙眼树不远处的地方摆放几个黑褐色的木箱子,我们几个孩子起先还不懂,经常绕着这几个木箱捉迷藏,等到有一天,箱子外总有蜜蜂爬进爬出,偷偷掀开盖子里面竟然是蜂窝还有金灿灿的蜂蜜,我们这才知道那是蜂箱。在龙眼树下纳凉或缝缝补补的婆们婶们总要提醒我们这些孩子离蜂箱远点,别去招惹蜜蜂,免得被蜜蜂蜇伤。盛夏,龙眼树愈发郁郁葱葱,串串黄豆般大小的小龙眼挂满枝头,一派丰收范十足。龙眼果实渐渐成熟,总会有调皮的男孩子偷偷地爬上树去摘着吃,我们几个女孩子不会爬树只能干瞪眼,就希望台风赶紧来,台风过后,树底下争捡掉落的龙眼似乎也是我们儿时莫大的快乐,这不就提前品尝到龙眼了吗?即便那时的龙眼还没成熟,甚至果核还是白色的,但是果肉已有清清的甜。每次风雨过后,还没等我们去捡龙眼,爷爷的肩头上已经搭着一包用他的黑白条纹腰巾裹着的龙眼踏进家门了。其实,不管台风来不来,这时候爷爷总要去山坡上砍几捆荆棘(带刺的一种植物)横七竖八地围住龙眼树干,不是怕龙眼被偷摘,而是防止孩子们爬树摔伤了不好交代。
夏末,龙眼树挂满滚圆金黄的果实,把桀骜的枝条压弯了腰,此时我们最盼望的是爷爷早点宣布:“龙眼明天开摘!”当爷爷号令一出,我们姐妹几个就兴高采烈地跑去告知堂兄弟们,叔婶们早已备好竹竿刀、竹篮、箩筐。大家齐心协力搬开一根根横放树头的荆棘,摘龙眼的戏份也就正式开演了。堂兄弟们个个身手敏捷,爬上树轻而易举,但对于我来说,爬树好比登天——难。堂兄弟们爬上树站稳后,树下的婶们就把竹篮箩筐用竹竿撑起递给树上的。堂兄弟们把竹篮箩筐吊在树干上或支在树杈间放稳,一旦箩筐放满就用吊绳放下来,空的箩筐再吊上去。我们在树下的一边捡拾掉落的龙眼,一边大声地吆喝树上的哪串好,哪串怎么摘,还不忘把果实往嘴里塞,那甜滑鲜美的味道一时满足了等待数月的馋相。
一个又一个收获的旺季,支撑着我们的成长。每逢龙眼果实采摘下来,爷爷总是把龙眼平均分到叔婶们家,虽然我们家里多几口人也没有多拿一些。分回来几箩筐龙眼,奶奶又开始忙活了。奶奶用麻绳把龙眼扎成一束一束的,然后我们姐妹仨把龙眼一家一束送去,奶奶还会特别交代我们哪家孩子多的要给那个大束的。剩下的龙眼奶奶就一颗颗摘下来放簸箕里端到屋顶去晒太阳,晒到半干才好吃呢!这些龙眼半干品就是放学后的零食,想想当时的我们也是幸福的。等龙眼干晒到可以收藏时,奶奶就把龙眼干装进缸里。我们想吃时都可以自己去缸里掏出来吃。当邻居带孩子来我家玩时,奶奶也常常毫不吝啬抓出几把塞给他们吃。一声声“媚姐,你人真好!”奶奶听得心花怒放了。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们已离开故乡多年,不知那两棵龙眼树是否依然安好?又是龙眼花开结果的时节,回想起当年在树下忙碌穿梭的爷爷与奶奶,甚是怀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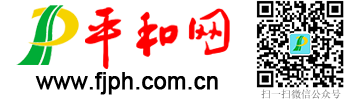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