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寨无名楼
它依然耸立在那里,作为一种时光流逝的证据存在。不论是春天花红柳绿的浸淫、还是夏日狂狼的追逐、或是秋日的黄金甲披身、还是冬日里刺骨寒风的渗透,它仍然那么健美、平静,甚至以一种冷漠的姿态,坦然接受光阴在它身上肆无忌惮地掠夺。它很安静,却似洪钟震耳,它就在眼前,却那么的遥不可及,高贵与落魄在它身上并存,让人不敢轻易接近。可是,每当我静静地坐在它残缺的臂弯里时,却能想起在年幼时,依偎在父亲怀里时的那种温暖与安定。
事实上,它应该是有名字的,只是岁月太远,人烟荒芜,光阴隐藏了它曾经的姓与名,便成了一座无名的土楼。它如落魄的公主,是千百年前,埋名隐姓在平和县五寨乡的皇家贵族。曾经,满腔热血的人们也想要重新去修葺、去还原它的样貌,可是最终发现,任何新物件挂在它身上时,显得是那么的滑稽、那么的肤浅与轻飘,就像给古稀老人配了一件时尚的超短裙,于是,所有的动作戛然而止。
闽南的土楼太多了,多到让我总是混淆了它们的名字与所在的地理位置。第一次认识五寨乡的那座无名楼,纯属偶然,但只是看了那么一眼,就足够让我产生了接下来无数次造访的理由。
每年写生,都习惯以秋季伊始作为开端。我便会从画室的某个角落里,拖出那个灰扑扑的小画箱,拂去它一身的尘埃,把它从混沌的睡梦中拍醒。这个画箱,哪怕是跟随了我十几年,我也从没有想过要为它取名,那么,以后就也叫它“无名”吧!它的存在,如同心有灵犀的老友,属于有事联系、无事消失之列。在那年秋天的某个傍晚,忽然接到老师的电话通知,告知他老人家已在五寨乡的无名楼写生,于是上网搜索了一下位置,居然在距离我不到三十公里的一个乡村里,于是,第二天一大早便驱车前往报道汇合,紧赶慢赶中,打翻了一杯牛奶早餐,溅湿了我的蓝布裙摆。
闽南人的宅舍,通常是“坐北朝南”,而眼前的这座土楼,却是“坐南朝北”,是否意味着另有深意?或许楼主的寓意是:“身在南方,心系北方家园”?如今的无名楼,除了楼门右边还保存十余间楼房外,四周只剩下了光秃秃的高大楼墙,一座四方形内楼,就这么悠然矗立在楼中央,给人一种苍凉空旷之感,豪迈中,竟见寂寞。
闽南四季的温度与景色,边界感并不强,让人感觉有些暧昧不清。这都已经入秋了,依然绿意汹涌,尤其是那依偎在墙角下的那丛芭蕉树,从断墙的矮处,悄悄地向外探出嫩绿的叶片。本该低调匍匐的藤蔓,顺着墙角,悄悄攀爬上腰杆笔直的桉树,缠缠绵绵,在不经意间,已拥抱住整个树干,飞鼠、鸟雀殷勤地充当了它们的媒妁,叽叽喳喳地在绿荫之中来回穿梭,传话不休。
初秋的阳光,像薄薄的羽毛,柔柔地轻抚被光阴剥削过的黄色斑驳墙体,散发出黄金般闪耀的光芒,明亮但不刺眼,使得我一时走神,竟忘记了手中的画笔。恍惚中,仿佛能看见那些当年流落民间的皇族贵胄,在奴仆们拥簇下的繁华镜像,嬉闹声、吵嚷呼喝声、锅碗瓢盆碰触声……随风入耳,我站在危墙下,听着、看着,仿佛被那声浪所触、被人潮卷裹,踉跄着在拥挤的人群中茫然四顾,我深吸了一口气,挣扎着退了出来。我有些失落,在那短暂时空错位的电光石火里,没能抢拍下几个镜头。
四季的风,把无名楼的馨香向八方传播,在古老文明的召唤与牵领下,诗人们来了,画家们也来了,他们就像蜜蜂或者蝴蝶,总能凭着灵敏的嗅觉,寻到甜美的蜜汁。在这里,诗人们寻找到了诗的源泉、画家们寻找着画面的灵感,他们一次次地来到这座雄健苍凉、酷似“军事城堡”楼墙下,倾听回荡在时光河流里,那清脆的马蹄声。
我爬上了被风雨削平了锐气的墙头,俯视着墙角茂密的草丛。起风了,秋风吹得脚下的绿波汹涌,我仿佛听到了海浪拍岸的声音,不,那应该是隐藏在残墙缝隙里的魂魄在啸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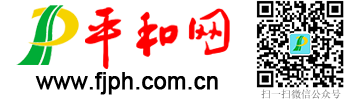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